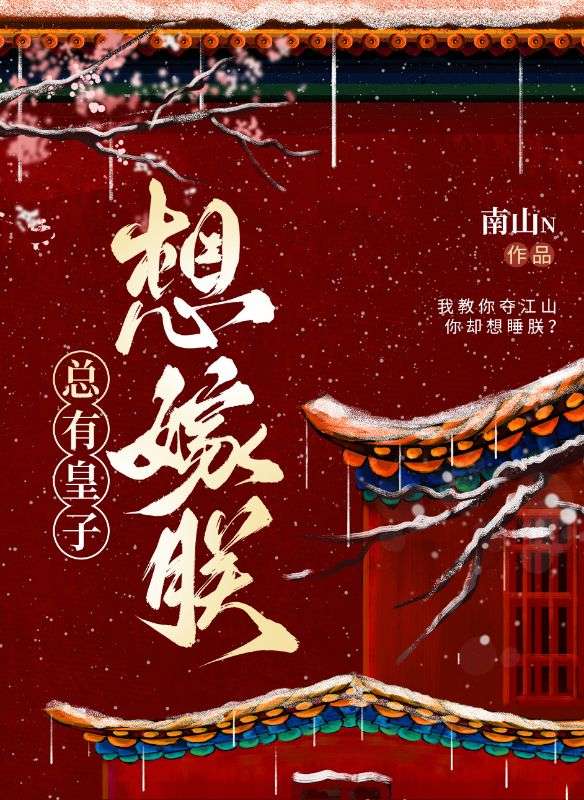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22章
討伐
豆腐巷在一聲雞叫後開始新的一天。
雨過天晴,空氣帶著秋桂的幽香,分外清新。
第一個早起準備去支攤的人瞧見巷子邊躺著一個人,走近一看驚得後退了一大步:“王,王娘子,你怎麼了?!”
王娘子被斷了手筋、腳筋,割了舌頭,黥了麵,這是她應得的報應。
將離看在她還有三個孩子要養的份上,留了她的命。
她喚回琉羽,帶人去東郭村破廟把將不棄和柳翠筠轉去他處看押起來,自己掉頭回將府。
將老夫人、將之瑤看到她就像見到了鬼似的,尖叫不迭。
“你沒死!你怎麼還沒死!”
“娘呢?大哥呢!你是不是殺了他們了?!”
將離嫌吵,直接一個耳光把將之瑤扇閉嘴了。
“從今日起,我就是將家家主。你們再敢對我動手,將不棄和柳翠筠就別活了。聽懂了嗎?”她頭一次砸茶盞。
汝窯,一擲千金,砸起來的確爽。
將老夫人嚇暈了過去。
將之瑤戰戰兢兢地靠過去,攙住將老夫人,大氣都不敢吭一聲。
將離轉身回了翠竹軒,雙慶看到她愣了愣神,她直接無視,“送水,我要沐浴更衣上朝。”
“是,是。”雙慶垂著手,低著頭迅速退下。
這個世道就是這般弱肉強食;你若隻是強一星半點,多的是財狼虎豹圍著你想一口吞噬;可你若強得可怕,他們隻會畏懼地跪下,俯首稱臣。
再一次站在大殿之上,將離比過往都漠然。
整個早朝太子和李承昊的視線都掛在她的身上,尤其是李承昊,星眸濃得像一團墨,將離不由自主眼角瞥過,這墨又化成利箭,紮得她生疼。
她不能看,立即抽回了視線;迎頭又對上太子滿懷歉意和熾熱的目光,心又嫌惡地往下一沉。
如此反複,令人心煩。
又過了幾日,早朝上,她終於見到了風塵仆仆的孟賀嶂。
二十多年過去了,他早已不是那個意氣風發的探花郎;邊塞的風把他的棱角磨平,他就像苦大仇深的西北漢子一樣,時刻眉頭擰成河川,又黑又幹瘦。
他手捧著木盒,跪地涕淚:“陛下,臣送太傅頭顱還朝了!”
陛下斷了腿在龍座上無法起身,可還是情不自禁向前撲了過去,淚雨滂沱,潘德海扶住了他,“陛下,保重龍體啊!”
“太傅!朕的太傅啊!錫人可惡!朕要殺光他們為太傅報仇!”
群臣:“陛下,保重龍體!”
孟賀嶂轉身將木盒遞給了將離:“尚書大人,卑職沒有保護好恩師,卑職愧對恩師,愧對大人!”
將離顫抖著手接過木盒,一時凝噎,竟不知該說些什麼。
周遭已經起了低低的啜泣聲,都是太傅生前摯友和門生。
“孟大人,多謝!”
將離滿肚子的疑問都放在了一旁,潘德海從台階下來,對她頷了頷首後,掀開了木盒。
腐爛的氣息再一次彌漫在大殿中。
頭顱高度腐爛露出森然的白骨,零星掛著幾點肉皮,木盒底下是腐爛的肉泥和頭發。
有大臣隻瞥了一眼憋不住嘔吐,被殿前侍衛抬了出去。
皇帝不忍直視,揮了揮手,潘德海又將木盒蓋回去。
“愛卿於何處發現的太傅頭顱?”
孟賀嶂跪下回稟:“臣派人去邊境打探,有人曾看到流竄的錫兵過境,將一個頭顱似的物件當球踢。臣帶府兵飛速趕去,他們丟下頭顱聞風而逃。臣細細辨認後,才確信是太傅……”
孟賀嶂泣不成聲,說不下去了。
將離鬥大的眼淚無聲掉落在木盒之上,淚水順著木頭紋理暈開一朵朵暗蓮,一個恨字已經無法表達此刻的心境。
太子想安慰她,卻又猶猶豫豫不敢上前。
李承昊直接出列奪過木盒,對皇帝道:“陛下,太傅身首不宜分離過久,當盡快入土為安、早入輪回。當日是北冥鐵騎送太傅靈體還都,太傅頭顱入殮一事就由臣來繼續完成吧。”
皇帝深以為然:“長煦說得對,事當有始有終。此事就交由禮部與你共同督辦,孟卿既已歸朝,儀式就由你這個員外郎來主持吧。”
“臣謹遵聖命。”孟賀嶂、李承昊跪地叩首。
將離低低地道了聲謝:“有勞了。”
李承昊凝眸看向地麵的磚石,它們被常年踏入大殿的朝臣來回踩踏,磨得油光發亮,他們靜靜地聽著大慶朝頂層機密,冷眼旁觀王朝的悲歡離合。
他本想爭口氣也如磚石這般冷著他,如同他對他一樣,可這個人突然哭得梨花帶雨,他受不了。
他隻當自己是見不得人掉眼淚,粗著嗓子假裝淡然:
“我就是塊磚,哪裏需要往哪裏搬。用不著謝。”
將離動了動唇,突然,孟賀嶂朗聲:“臣另有本啟奏。”
“哦,何事?”皇帝擦了擦眼角。
孟賀嶂從寬大的官袍袖口中摸出一份折子:
“臣要告發葉州刺史屠光,私煉鐵器暗中招兵買馬意圖謀反。這是臣收集的證據,屠光貪腐稅銀、魚肉百姓,欺上瞞下,與錫人多有勾結,太傅之死更與他難逃幹係。臣叩請陛下嚴懲奸佞,為葉州百姓除害!”
將離沒料到孟賀嶂會先發製人,她剛想開口,李承昊先一步問道:
“孟大人,謀逆的罪名可不小啊。你做了二十年的刺史府師爺,為何從前不說,今日才說?”
“陛下!臣的確慚愧。臣做師爺二十年因不會阿諛奉承為屠光不喜,因而日常僅處置些基礎文書,並不受重用。這些年葉州百姓多有冤屈卻訴訟無門,臣也私下向禦史台、諫院匿名舉報,可書信卻石沉大海。若非太傅在天有靈讓我有此機緣回雀都,臣至今仍不知該如何告發他。陛下,此番回京,屠光還扣押我的家人,為的就是怕我告發他。”
“豈有此理!謝世忠!速領一隊人馬去葉州,若查實屠光謀逆,就地處置!”
“是!”謝世忠領命,大殿之外突然傳來急報。
“陛下,葉州屠光自立為洪烈王,反了!”
孟賀嶂麵色慘白:“微臣家眷如何了?”
信使吞吞吐吐:“孟大人娘子和一雙兒女皆被祭旗了!”
孟賀嶂慘叫一聲昏死了過去。
潘德海小跑過去:“快,快喚太醫啊!”
將離和李承昊忍不住對視了一眼,心有戚戚焉。
亂世之下,婦孺何其無辜。
“混賬!”皇帝撐著龍案站了起來,氣得渾身發抖:“屠光小兒!竟真敢……咳咳……”
“陛下!保重龍體啊!”
皇帝狂咳不止,喘息如擂鼓,珠簾後的太後沉聲道:“諸位臣公,屠光謀逆,該當何罪?”
蕭相國出列:“太後,陛下,屠光本是西北一介莽夫,若非陛下賞識如何能居刺史之位。他不但不感激還起了不臣之心,如此目無君父,當五馬分屍。臣叩請必陛下出兵討伐逆賊,以正朝綱!”
眾臣附議。皇帝緩了緩咳嗽,眉心黑氣鬱結:
“諸位愛卿看,該派誰去討伐這逆賊?”
蕭相國:“葉州有八萬守城軍,實力不可小覷。按說北冥的涼州大營離葉州最近,可李長白如今還在同錫人作戰,若反攻葉州,勢必拖累前線;臣認為當派平西將軍紀長庚率兵討伐最為合適!”
紀長庚是太後和蕭相的親妹夫,但其人驍勇善戰,不遜於李長白,眾臣紛紛頷首,皇帝也覺得合適:“有道理。平西軍在睦州的前鋒營距離葉州最近,即刻給紀長庚發八百裏急報,令他為統帥,平定葉州,誅殺反賊屠光!”
“是!”兵部尚書蕭定邦出列領旨。
他是蕭相國的侄子,蕭家這一輩裏沒幾個能扶的上牆的,惟有這個蕭定邦還算機靈,相國推著他掌著兵部,紀長庚又占據西境,大慶的兵權由始至終都緊緊握在太後的手心裏。
早朝因為屠光謀逆匆匆結束。
李承昊手捧著木盒往外走,將離跟在身後。
風起微瀾,單薄的官袍有些漏風發冷,將離望著他高大的背影,沉了沉氣:“木盒給我,入殮之前我帶回府供在祠堂。”
“將不棄,說合作的是你,拒人於千裏之外的也是你。當初你接近我不是挺熱情的,怎麼,太子要監國了,你就過河拆橋了?”
將離由得他發火,隻接過木盒依舊冷淡:“我答應你的不會食言。待太子登基,我一定會讓他放你回北冥的。總督大人,你我之間的合作已經結束了。”
“結束?”李承昊蒙了,“那小黑呢?你不要了?”
“不要了,歸你。”將離往前走,沒有停留。
李承昊一口氣上不來,抬腳跟了上去:
“那河邊那塊破地呢?你讓我要過來,也不要了?”
“不要了。給你。”
你……李承昊氣得心梗,“將不棄,你有種!”
玄暉生怕他又要衝過去剝衣服打架,立刻抱住他的腰:“爺,冷靜!冷靜!”
“冷靜個屁!”李承昊掙紮著踹腳,牙根發癢,“我要打死這個狗東西!”
將離剛走到宮門口,東宮長隨天祿小跑上前:“大人,太子殿下要見您。”
將離看了看手中的木盒,歎了口氣,遞給了雙慶:“通知府裏,請廣佛寺聖僧來念經超度。”
“是。”雙慶接過後問道,“此番可要再設靈堂、搭棚設祭?”
“不必了。爹素來清儉,不喜奢靡浪費。”
將離說完,跟這天祿往東宮而去。
太子見到她,掩不住欣喜。
但想到太傅頭顱之事,又覺得喜上眉梢有些不合時宜,便摸了摸鼻子訕訕道:“阿離,你要節哀。”
“太子殿下喚我來,所為何事?”
“前幾日你生我氣,孤召你來東宮你也百般推辭;孤想去將府找你,可又怕你不肯見我,輾轉難眠。這滋味太難受了,你可原諒孤了?”
將離拱了拱手:“太子殿下言重了,臣怎敢生您的氣。”
太子很高興,“孤就知道阿離識大體。前幾日我同你哥提過選妃之事,他可曾告訴你?”
“告訴我?”將離蹙了蹙眉,“你同他挑明了我的存在?”
“自然。我與他六歲共讀,情誼非常人能比。他有你這樣優秀的妹妹又不是什麼見不得光的事。更何況你替他上朝議政,更立下救駕之功,讓他成了大慶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尚書,他感激你還來不及呢。”
將離唇微微一動,心下冷笑,感激?
感激地提前給她找好葬身之地了。
“選妃之事殿下不是已有主張了?”將離不想摻和。
“是。是。”殿下來回搓著手踱步,“你不止救了陛下,還救了孤。孤同將不棄說了,孤要立你為太子妃!”
將離以為自己聽錯了,“我?太子妃?”
“是吧?孤就知道阿離定會歡喜。阿離,你不是說想要個身份嗎,如今孤就給你這個身份。你有勇有謀,是太子妃的不二之選。”
“可你要娶的不是將之瑤嗎?”將離頭都要炸了,這是什麼和什麼啊。
“胡說,孤何時說過要娶阿瑤?孤說的太傅之女,從頭到尾指的都是你。阿離,這麼久了,難道你沒看出孤對你的心意嗎?”
太子上前一步,伸手攬過她的腰,俯身想要親她。
將離要推開他,正巧,門外咣當一聲,太子極速鬆開手。
是將之瑤,她手中的食盒掉了,湯汁灑滿一地。
她極度震驚,太子要娶的人不是她,是將離?
將離聞到老火燉鴨的香味,心生惋惜。
……浪費了一碗靚湯。
“殿下,你怎能如此對我!將離,我恨死你了!”
“阿瑤……”太子呼叫不及,將之瑤已經跑得遠遠的,人影都望不到。
太子搖頭,隻當她是鬧了脾氣的小妹妹,“她會想明白的。”
將離腦子嗡嗡作響,頗為無奈地看著他:“您想娶我?可我以什麼身份嫁給您?將家可從來沒有一個叫將離的女兒。”
“這個簡單,我想好了。”太子誤以為她答應了,喜不自勝。
“你以將之瑤的名義嫁入東宮,成了太子妃,誰還敢質疑你。阿瑤嘛,我就讓她換個身份,比如將家收養的女兒啊,回頭再賜個縣主之類的封號,尋一門好親事。這不是兩相得宜嘛!”
將離笑出了聲。
“這就是你說的讓我見天日的法子?”
太子被她笑得有些莫名,“怎麼,不好嗎?”
如此一來,他娶的是將家嫡女,而將離就是將家嫡女,沒毛病啊。
“可我叫將離,不叫將之瑤。”
太子一揮手,雲淡風輕:“稱呼罷了,有何所謂。日後孤登基,你就是母儀天下的皇後,還有何人敢直呼你的名諱!阿離,你別鬧小性子,這是孤想的最完美的法子!”
將離對他徹底失望了。
“原來你說讓我堂堂正正活在陽光下,就是頂著別人的名字嫁給你?”
太子怔了怔,“難道這不是你期望的嗎?”
他給了她最至尊的太子妃,難道還不夠堂堂正正?
將離步步向門口退,深吸了一口氣:
“太子厚愛,臣無福消受。告辭了。”
太子心一急,失去了往日的儒雅,衝上前抱住她不撒手:“阿離,你怎麼了?你別走,我們說清楚。”
“太子殿下,請自重。”
將離惱羞成怒,狠狠踩了他一腳,太子一個趔趄摔倒在地上。
恰逢此時東宮內監帶著丁長卿走了進來。
兩人瞪大了眼珠子,偌大的園子連個遮擋的地方都沒有,一時竟不知該往哪裏躲。
將離冷臉拂袖而去。
太子毫不掩飾一臉淒哀之色:
“哎,她怎麼就不懂孤的苦心呢。”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
丁長卿浮腫的雙眼頃刻就亮了。
“殿下,臣有一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