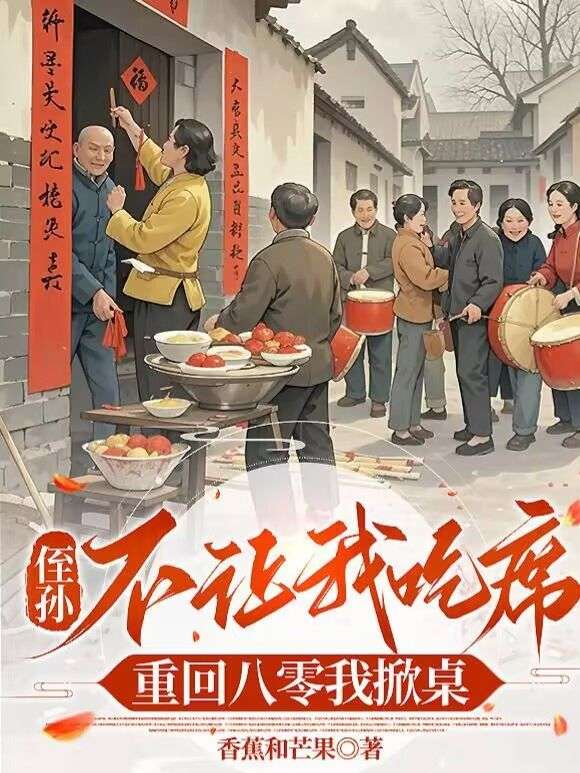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4章 隻要肯彎腰,遍地都是黃金
第14章 隻要肯彎腰,遍地都是黃金
莫雲嵐站在門口,手裏的塑料盆還在往下滴水。
屋裏黑漆漆的,隻有那個奇怪的鐵疙瘩在瘋狂旋轉,攪動著滿屋子的熱浪。兩個兒子興奮得嗷嗷叫,賀長征坐在陰影裏,指尖忽明忽暗,那是煙頭的火光。
“媽!你看!爸修好了!風特大!”賀傑衝過來,拽著莫雲嵐的衣角往風扇跟前湊。
莫雲嵐沒動。她借著月光,看清了那台拚湊起來的機器。
醜。
真醜。
底座鏽跡斑斑,扇葉是鐵皮剪的,連個網罩都沒有,轉起來像個隨時會切斷手指的斷頭台。
但那風,是真涼快。
“關了。”莫雲嵐把盆放下,聲音不大,卻透著股威嚴。
賀長征手忙腳亂地拔了插頭。
嗡嗡聲戛然而止,屋裏瞬間安靜下來,隻剩下扇葉慣性旋轉的沙沙聲。
“媳婦,我......”賀長征站起來,像個做錯事的孩子,搓著那一手油泥,“我就是試試。這就拆了,明天拿去賣廢鐵。”
“賣廢鐵?”莫雲嵐走到桌邊,拉開燈繩。
昏黃的燈光灑下來,照亮了賀長征那張忐忑的臉。
“一塊二買回來的,你打算賣幾毛?”莫雲嵐伸手摸了摸風扇滾燙的電機後蓋,“這玩意兒轉得這麼歡,你當廢鐵賣?賀長征,你腦子裏裝的是漿糊?”
賀長征愣住了:“那......那咋辦?”
“明天一早,去西關那個自由市場。”莫雲嵐也不廢話,伸出三根手指,“賣這個數。”
“三塊?”賀長征鬆了口氣,“行,能賺一塊八,夠買兩斤肉了。”
“三十。”
賀長征手裏的煙頭掉在了腳背上,燙得他一哆嗦。
“多少?!”他眼珠子瞪得像銅鈴,“三十?搶錢啊?供銷社一台新的華生也就一百出頭,還得要票。我這破爛拚的,敢要三十?”
“你也知道要票?”莫雲嵐白了他一眼,拿起毛巾擦頭發,“現在是大夏天,供銷社的風扇早就斷貨了。有錢沒票的人多得是,熱得睡不著覺的大有人在。三十塊,不要票,這就叫——”
她頓了頓,吐出四個字:“降維打擊。”
賀長征沒聽懂啥叫降維打擊,但他聽懂了三十塊。
他一個月工資,加上全勤獎和高溫補貼,也就三十八塊五。
這一晚上,就能掙一個月工資?
“這......這能行嗎?”賀長征還是虛。
“行不行,死馬當活馬醫。”莫雲嵐把兩個孩子趕去睡覺,然後指著那裸奔的扇葉,“不過這樣不行,太危險,容易出事。家裏還有鐵絲嗎?給它盤個罩子。”
賀長征看了一眼那堆廢品裏剩下的漆包線和一截粗鐵絲。
那是鉗工的本能。
隻要有材料,就沒有他做不出來的東西。
“有。”賀長征把煙頭踩滅,眼神重新變得聚焦,“不僅能盤罩子,我還能給它噴層漆。床底下有半瓶以前廠裏剩下的防鏽漆。”
這一夜,賀家的小屋裏,叮叮當當的聲音響到了後半夜。
......
第二天,天還沒亮。
東邊的天空像是被潑了一層墨藍色的水。
賀長征背著一個大布包,鬼鬼祟祟地出了門。
包裏沉甸甸的,那是經過他一夜“整容”的風扇。
粗鐵絲被他彎成了標準的同心圓,焊接點打磨得光溜溜的,最後噴了一層綠色的防鏽漆。雖然看著還是有點土氣,但至少像個正經工業品了。
西關自由市場,其實就是一片自發形成的集市。
在這個年代,政策剛放開,但也還沒完全放開。這裏魚龍混雜,賣雞蛋的、賣煙葉的、賣自家編的竹筐的,都擠在一條狹長的巷子裏。
賀長征找了個角落蹲下。
他心臟跳得厲害,像是要從嗓子眼裏蹦出來。
這是他這輩子第一次幹這種“投機倒把”的事兒。以前在廠裏,他最看不起的就是這種二道販子。
可現在,為了那三十塊錢,為了兒子下個月的夥食費,他把那張老臉揣進了褲兜裏。
他把布包解開,露出那台綠油油的風扇。
沒敢吆喝。
他隻是找了個借口,跟旁邊賣插座板的小販搭訕,借用了人家的電源插口。
“嗡——”
風扇轉了起來。
綠色的扇葉化作一道虛影,強勁的風呼嘯而出,把旁邊賣旱煙老頭的一堆煙葉吹得漫天亂飛。
“哎喲!好大的風!”老頭罵罵咧咧地去撿煙葉,但眼神卻直勾勾地盯著那台風扇。
這一開,就像是在平靜的水塘裏扔了塊石頭。
周圍幾個攤主和路過的行人都停下了腳步。
“這是啥牌子的?風這麼硬?”
“看著像華生,又不太像。”
“大兄弟,這玩意兒賣嗎?”
賀長征緊張得手心冒汗,他咽了口唾沫,伸出三根手指:“賣。三十。”
“三十?!”
人群裏發出一陣吸氣聲。
“太貴了!搶錢呢!”
“就是,看著跟舊貨似的,哪值三十?”
賀長征臉憋得通紅,正想解釋這電機是好的,這線圈是重繞的。
“讓讓,讓讓!”
一個穿著白襯衫、腋下夾著個公文包的中年男人擠了進來。
這人滿頭大汗,襯衫後背都濕透了,一看就是那種坐辦公室但沒空調受罪的主兒。
他盯著那台風扇,眼睛都在放光。
“這風扇,不用票?”中年男人問了一句。
賀長征搖搖頭:“不要票。”
“能試多久?”
“隨便試,燒了我賠你。”說到技術,賀長征的腰杆子挺直了,“這是工業電機改的,連續轉三天三夜都不帶發燙的。”
中年男人伸手在風扇前試了試風。
那是真涼快。
他在單位辦公室裏,那個吊扇轉得跟老太太紡紗似的,根本不頂用。家裏更別提了,老婆孩子天天晚上熱得睡不著,吵得他頭疼。
他又看了看這風扇的做工。
雖然油漆有點糙,但那網罩焊點均勻,一看就是老師傅的手藝。結實,耐造。
“二十五,我拿走。”中年男人開始殺價。
賀長征剛想點頭。二十五也不少了,那是暴利啊!
但他腦子裏突然響起了莫雲嵐昨晚的話——“少一分都不賣,愛買不買。”
賀長征咬了咬牙,硬邦邦地回了一句:“三十。少一分不賣。”
中年男人皺了皺眉,似乎在權衡。
周圍的人都在起哄:“別買!太黑了!這破玩意兒哪值三十!”
賀長征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怕這人走了。走了可能今天就開不了張了。
就在這時,中年男人從兜裏掏出一個手絹包。
“行,三十就三十。”他數出三張嶄新的“大團結”,遞到賀長征麵前,“但這插頭好像有點鬆,你得給我弄緊點。”
“沒問題!”
賀長征接過錢,手都在抖。
他從隨身的工具包裏掏出鉗子,哢吧兩下,把插頭銅片校正,又把風扇電源線順好,恭恭敬敬地遞給對方。
中年男人提著風扇,像抱著個寶貝似的,心滿意足地擠出了人群。
賀長征站在原地,手裏攥著那三張帶著體溫的鈔票。
三十塊。
真的是三十塊。
昨天下午,這還是一堆躺在廢品站裏、論斤稱的一塊二毛錢的垃圾。
經過他一晚上的敲敲打打,就變成了三十塊錢。
二十八塊八的利潤。
他在廠裏累死累活幹一個月,連個屁都不敢放,還要看車間主任的臉色,才拿三十八。
而現在,僅僅是一晚上。
一種前所未有的衝擊感,像電流一樣擊穿了他的天靈蓋。
什麼麵子?
什麼投機倒把?
去他媽的!
手裏這硬邦邦的票子,才是真理!
這錢能給文文買肉吃,能給家裏買煤球,能給媳婦扯塊花布做裙子!
賀長征深吸一口氣,把錢小心翼翼地揣進貼身口袋,又按了按,確認不會掉出來。
他收拾好地上的工具包,轉身就走。
“哎,大兄弟,這就回去了?”旁邊賣插座的小販眼紅地問了一句,“家裏還有沒有這種風扇?我也想要一台。”
賀長征停下腳步。
早晨的陽光照在他那張滿是胡茬的臉上,那雙原本有些渾濁、唯唯諾諾的眼睛裏,此刻燃燒著兩團火。
那是野心的火苗。
“沒有了。”
賀長征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煙熏黃的牙齒。
“不過,很快就會有的。”
他沒往家的方向走。
他轉了個身,大步流星地朝著縣城廢品收購站的方向走去。
既然一塊二能變三十。
那要是把廢品站裏的那些破電機、壞收音機全都包圓了呢?
賀長征覺得自己的血都熱了。
活人,真的不能讓尿憋死。
隻要肯彎腰,遍地都是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