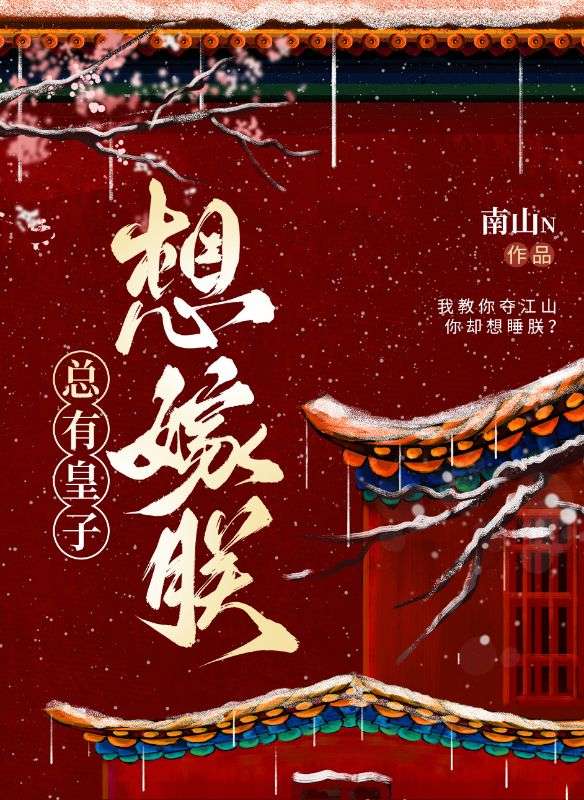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6章
鞭痕
延壽宮,太後輕啜著參茸當歸養顏湯。
烏鬢雲髻、容顏豔麗,雖已過六十卻保養得宜,美人未遲暮全靠銀子堆出來,雍容貴氣依舊,隻是臉上的笑有些刻薄,帶著骨子裏的輕蔑。
“紀雲茵這個賤人生出來的賤種,他還真當一回事,誰知道是不是他的種?”
太監慕連點頭哈腰:“誰說不是呢。李世子人高馬大的,瞧著也挺像北冥王。您說,陛下該不會起了別的心思吧?”
“嗬,他不敢。他當雀都世家全都是死的不成?”太後冷下眉眼,細長的眸子裏隱約閃著火苗,眯眼時眼角幾道細微的魚尾紋承載著怒意,“當初可是我們蕭家費盡心機將他從一個無人問津的庶子扶上這帝位,他想過河拆橋,沒那麼容易。除非哀家死,六大世家絕了戶,否則,北冥的野種休想登上這帝位!”
慕連屈身接過空碗,垂著眉安撫著:“您與陛下雖不是親母子,可同患難過的,過去挨了多少苦日子啊!這情分遠勝過親生了。陛下心裏頭有您呢!”
“哎,共患難有什麼用,誰坐在這位置上,不想獨攬天下。非是哀家不放權,實則是他身子弱,哀家怕他太操勞。”
太後閉著眼睛,揉了揉額角。
慕連順勢將碗遞給身後小太監,自己繞到太後身後揉肩按摩,“是,是,這麼多年您費心勞力的,奴才都心疼了,娘娘,可要保重鳳體啊,您瞧,這鬢邊都有一根白頭發了呢。”
“快拿鏡子來。”太後眉頭一挑,示意婢女取銅鏡來,細照之後手指拈著一根白發,心生唏噓,“歲月不饒人啊。”
她的目光一凜:“他想磨刀,哀家就送他一把刀。去通知相國,該辦的事得操辦起來了。”
“是。”慕連躬身退下。
走出宮,李承昊和崔無咎一人一馬,慢步向前。
“陛下對你還真是偏心,你是不是給他灌迷魂湯了?”
崔無咎越想越覺得不是滋味:“你看看陛下說的。啊,無咎也去,同你作伴。本公子可是名震雀都的查案高手,怎麼成了你的跟班了?”
“嗬,查案高手,你倒說說,查出什麼屁來?”李承昊騎在馬上陰沉著臉,看誰都像欠他八百萬似的。
“我真查出東西了。但周開原不讓我查下去。”崔無咎道,“湧安的死,必是熟人所為。”
李承昊停住馬,挑眉:“細說。”
“他的傷口是近距離造成的,創口自下向上,凶手的身高低於湧安,出手幹脆利落,刀口入腹還旋轉了三周半,嘖嘖,狠辣。”
傷口都捅成爛泥了,他費了一番功夫。
李承昊頭一回拿正眼瞧他,“有點東西。”
“厲害吧?”崔無咎舔著臉,“把那豹子給我吧。”
他看上了,雀都養狗的多了,養豹子那可是頭一份,帶出去倍兒有麵子。
“不成,想都別想。”李承昊一口拒絕。
“那我去找將不棄要。”崔無咎耍賴。
他認識將不棄,這個人平時傲氣衝天的,怎麼也和養豹子對不在一起。
“你敢找他,我現在就削你,信不信?”
李承昊丟了個凶狠的眼神,策馬飛馳。
“哎!幾日不見,你就這麼小氣了!還做不做兄弟了?!”
“不做也罷!”
“長煦,你來真的?”
“等等我啊!”
過了幾日,傍晚時分,將離上李府拜訪。
李承昊穿得花枝招展,藍色祥雲紋樣繡花箭袖圓領袍,腰身束著玉石腰帶,金色發冠鑲嵌藍色瑪瑙,整個人清朗雅致,和往日武將做派截然不同。
將離發愣,“總督這是發大財了?”
玄暉死死屏住笑,李承昊傲嬌地抬眉,“日日都這麼穿的,你沒瞧見罷了。”
“嘖嘖,闊氣。”將離頷首,搖著扇子進府,剛剛落座,親兵就上前奉茶,果子果盤點心齊齊擺開,琳琅滿目。
“侍郎,請。”
李承昊挑開下擺,做得端正挺拔。
“嗯……上好的雀舌,冷泡最為適宜。”將離很意外,“沒想到總督對茶道也頗有心得。”
李承昊撓了撓腦袋,這還是臨時抱佛腳請教崔無咎的,他家老爺子對茶道、香道書畫深有研究,他想著將不棄這種人講究慣了,學了幾招應付一二。
“一般般啦,隨手弄弄的。”
一旁的玄暉瞪大了眼珠子,差點叫出聲。
什麼叫隨便弄弄,蟹粉酥、荷花酥、水晶菓子這可都是他卯時就出門,輪番跑了好幾家點心鋪子買的啊!
李承昊橫了他一眼,殷勤地端起點心碟子,“吃啊,別客氣。”
將離淺笑,卻之不恭,“多謝。”
李承昊看著她的芙蓉桃花麵心弦微顫,“你讓我找的人有眉目了。”
將離眉頭一喜,“在哪?”
“被舒王的演繹班子帶去芙蓉山莊排舞呢,一時半會近不了身。我看,這趟避暑你不去是不成了。”
芙蓉山莊在未央湖心,來去須有船隻接駁,單獨進去找人過於明顯,隻能趁著避暑去才能掩人耳目。
這對將離來說,可不是什麼好消息,“去避暑啊?”
李承昊為她斟茶:“別猶豫了,顏直那老頭受傷了去不了。這福氣落你頭上,跑都跑不掉。”
受傷?將離簡直不敢相信,“何時的事兒?”
她同顏直一個部門的,早上見他還好端端的呢。
“他家不止有悍虎,還有個七十歲的老母頗不講道理。今兒婆媳不知為何時鬧了起來,那悍虎抄著香爐正好砸到了顏直的腦袋,嘖嘖,顏尚書頭被打破了,流了滿地血,急急喚了禦醫呢。”
將離點頭,難怪他知道,今日他在宮裏當值。
“顏尚書可真命苦。”聽起來怪慘的。
“這娶妻當娶賢,妻賢夫禍少,就是這個道理。將侍郎日後可萬萬別找個悍虎,就你這個小身板,可不禁揍啊。”李承昊朝他咧嘴嘲笑。
將離反唇相譏:“一張床睡不出兩樣人,總督這般野蠻,想來日後娘子也不是好欺負的。我看,還是多擔心擔心你自己吧。”
“嘿你這人,閑聊罷了,你怎麼還咒起我來了。”
將離抿唇淺笑,他添堵難受,她就高興自在。
李承昊也不生氣,見她笑了,又道,“留著用晚膳?今兒你有口福,崔無咎在這呢。”
崔無咎?將離倒是聽過他的名字,崔家的獨苗,國子監祭酒崔永真心尖上的小孫孫,好像在大理寺混了個差事吧。
見將離沒什麼反應,李承昊又道:“他有一手絕活,就是片生魚膾,薄如蟬翼,入口即化,你不試試他的手藝可惜了。”
將離還沒什麼反應,一旁的琉羽口水都下來了,“真那麼好吃?”
李承昊和玄暉都笑了。
“不好吃你打他,好吃你喊我爹,如何?”
琉羽舔了舔唇,拉了拉將離的衣袖,“大人,我怎麼覺得總督在坑我呢?”
將離搖頭失笑,“不要覺得,他就是在坑你。”
兩人閑聊了幾句,侍衛親兵很快在花廳支起桌子,開始布菜。
崔無咎興高采烈地端出一盆片好的魚膾,獻寶似的捧在將離和李承昊的麵前:“瞧瞧,夠不夠薄,透不透亮?”
“將侍郎,魚,就得這麼生著吃,脆、甜。你試試。”
將離舉箸夾了一片,對著落日的餘暉,魚片泛著淡淡的金光,晶瑩剔透,放入口中,輕輕一嚼,很有韌勁,齒頰留香,甚是清甜。
嗯……她情不自禁地讚許,又取了片遞給身後翹首以盼的琉羽,“嘗嘗。”
琉羽雙手捧著魚片送進口中,亮著一雙眸子猛點著頭。
李承昊很得意:“我沒說錯吧。”
崔無咎給大家斟滿酒,舉筷夾魚入腹,又痛快地舉杯一飲而盡,咂舌道:“人道天上龍肉、地下驢肉;可我覺得,再美都比不過這生魚膾,再佐以三杯兩盞淡酒,人生快哉!”
“聽聞這幾日大理寺忙得很,崔大人怎有如此雅興?”將離道。
崔無咎放下筷子,“長煦說你要來,非請我來露一手。我忙啊,這不是梅隴村死了一家子,我剛剖完屍呢,就馬不停蹄地過來了……哎,你們怎麼不吃了?是不愛吃嗎?”
花廳死一般的寂靜。
將離腹部微湧,“你剖了屍,洗手了嗎?”
崔無咎一臉無辜地攤開雙手,看了看將離,又看了看李承昊,“我這著急忙慌地趕來,忘了。也許洗了、也許沒洗……”
將離飛速起身,扶在門框開始劇烈嘔吐。
李承昊剜了一眼崔無咎,連忙跑到將離身後,伸手為她順了順背,又對玄暉道:“倒杯茶來給侍郎漱口。把這魚趕緊撤了。”
玄暉哦了聲,忙不迭去倒茶;
琉羽噙著星眸,剛咽下魚還在嘴裏回味呢,一看急了:“為啥撤啊,這不是挺好吃的。”
崔無咎哈哈大笑,拉著琉羽一同坐了下來:“還是你懂哥,甭理他們,咱倆吃。”
一場精心布置的席麵,草草了事。
飯後李承昊帶將離去看豹子,小黑的腿傷好了,正在籠子裏酣睡;海東青踩在竹籠上,忠誠得像個衛士。
將離小心翼翼地摸了摸海東青,霄沒有反抗,隻悶哼了聲,算是傲嬌地同意了。
“孟賀嶂要進京了。”將離沒有回頭,隻盯著霄看,不知在想寫什麼。
“你猜得對,他果然有問題。”李承昊嗓子低啞,聲線也嗡沉,同她一並蹲了下來,“我派人去葉州查了,葉州刺史屠光可不是好相與的,為人陰私刻薄,這二十年他倍受打壓,聽聞去歲他的老母病逝,都還是問人借的銀子才草草安葬。”
將離輕點頭,“他是天寶三年的探花,隻因為拒絕了蕭家的拉攏,就被排擠出雀都朝堂,著實可惜。”
孟賀嶂當年意氣奮發,相貌堂堂;打馬遊街引得萬千少女交頸接踵,隻為一睹他的風姿;蕭相國看中他的才學,想將女兒嫁給他,可孟賀嶂有個兩情相悅的青梅,一口回絕了。
此後,他的仕途屢屢受挫,直至發往偏遠的葉州刺史府做了個小小師爺至今。
將離的指尖來回在竹籠上擦拭,像是要擦掉竹棍上斑斑點點的淚痕,她的心頭有些亂,想起許多往事。
將正言惜才,屢次看著孟賀嶂的來信,為他歎息;也曾多次在深夜為他擬帖求同僚提攜,言辭切切。可朝堂上蕭相國一手遮天,縱然將正言三番四次舉薦孟賀嶂,最後都不了了之。
父親的死,會同他有關嗎?
她的指尖修長如蔥白,來回晃得李承昊有些心煩意亂,大手一摁,壓住了她的手:“這是淚竹,你擦破皮也擦不掉斑痕。想這麼多作甚,等拿到了信就都清楚了。”
容不得她抽回手,李承昊毫不客氣地撩開袖口查看傷勢,“淡了。”
先前紅色鞭痕已消褪,皓腕纖纖如玉潔白。
“說起來還得謝謝你的藥。”將離耳根通紅,“效果很好,哪來的?”
她身上有慧修給的各式各樣的藥膏,其中不乏有上好的金瘡藥,但李承昊給的也不賴,消腫去印還特別柔潤,疤痕淡了,新生的皮膚更嫩了。
“戰場刀劍無眼,受傷是常有的事,這金瘡藥是北冥軍醫特製的,加了羊油。你回頭再帶些去。還沒告訴爺,是哪個沒長眼的打了你?”
他想了好幾日都沒想明白,以將不棄如今身份,還有誰敢抽他。
李承昊見她眼神躲閃,神情不自然,驀地想起丁長卿他們的花路數,腦子一抽,
莫不是……閨房之樂?
他迅速鬆開將離的手:“貪玩也得注意分寸。”
貪玩?分寸?將離一頭霧水:“你喜歡玩鞭子啊?”
“變態才喜歡那玩意兒。”李承昊剜她一眼,抬腳就走。
“哎,這人,好好的,怎麼翻臉了。”
不遠處,崔無咎和琉羽捧著點心盤子嗑著瓜子,對玄暉說道:“長煦和將不棄何時這麼親近了?你看看,像小情侶鬧別扭似的。”
玄暉像是被點了穴,臉色比死了三天的魚還難看。
不會吧?爺喜歡男人?!
死了死了,這該如何跟王爺交代!
琉羽像隻小倉鼠,邊磕邊搖頭,“怎麼會,我家公子眼光高得很。”
玄暉一身傲骨瞬間立如鐵柱,沒好氣地抽回琉羽手裏的點心盤子:“我家公子眼光也高得很。”
琉羽:“哎!說話就說話,你撤什麼盤子啊!”
“哎!那蟹粉酥我還沒吃夠呢!”
玄暉:“吃你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