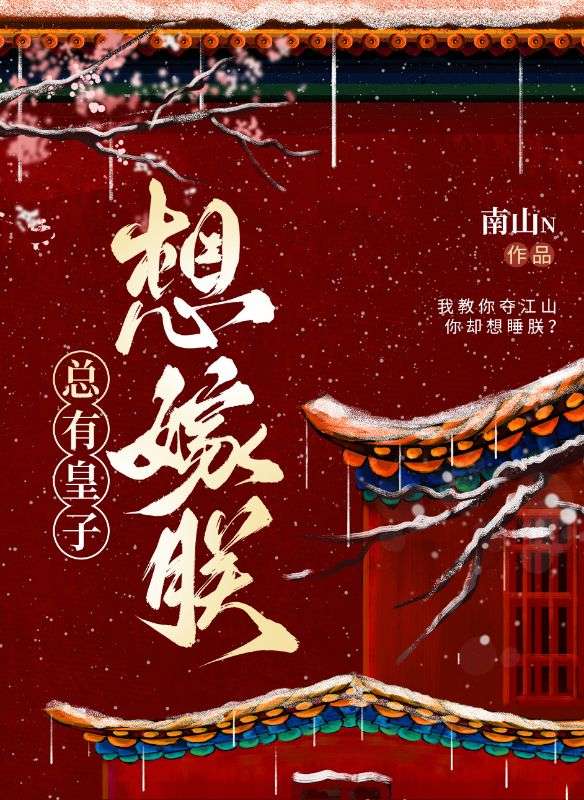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7章
彩芝
將不棄對避暑之事沒說什麼,隻是讓雙慶跟著去,盯著將離別犯錯。
將之瑤妒忌得很,這是極好的與太子親近的機會,她也想要去,鬧了將不棄許久。
將不棄沒法子,隻能跟太子請托,把將之瑤加入避暑名單。
如此一來,琉羽就不能去了。
將離安慰了幾句,讓她趁著這幾日再去查查湧安是否還有親人在世。
這廂李承昊也帶著玄暉踏上了芙蓉山莊。
從浮雲山腳下的碼頭望去,亭台樓閣飛榭連綿,雕甍繡欄,皆隱於山坳樹椏中;乘坐畫舫踏入島上,白石嶙峋、藤蔓爬牆,別有洞天。
皇帝對這座島情有獨鐘,原因眾說紛紜。
有說是陛下出生在這座孤島上;也有說陛下曾與當年不受寵的太後一並被流放至此島,臥薪嘗膽,終成帝業;也有說陛下年少時曾與心上人一同在此孤島生活過,等等。
總之,皇帝登基之後便在此島上大興土木,每年都會來島上小住一段時日。
將離搖扇同大人們寒暄周旋,將之瑤早已像花蝴蝶似的穿梭在女眷之中,炫耀她新買的珠釵和綺羅衣裳。
李承昊剛走近將離,立馬被舒王、丁長卿這幫紈絝給拖走了,兩人隻淺淺交彙了一下眼神,沒來得及說話。
雙慶盯著緊,將離隻能借著上茅房的當口,與玄暉交換信息。
彩芝與一眾樂班歌女都住在最西角落的廂房,今夜李承昊會以看中為由帶至下榻處,由將離來問話。
先前二人曾有過爭執。
李承昊:“憑什麼用我的名義?你也是男人!”
將離:“你花名在外,就從了吧。”
李承昊:“從什麼從,我守身如玉、寧死不屈。”
將離輕嘖了聲,不客氣地上下打量:“李承昊,你是不是玩多了,身子骨不行了?”
李承昊抓狂:“胡扯,爺強得可怕。”
“那不就得了,多符合你狂浪不羈的形象,見到女人就走不動道兒,帶回去春宵一夜很正常。我就不一樣了,我是斷袖、龍陽啊,隻喜歡男人,不喜歡女人的。”將離說得煞有其事。
李承昊總覺得被她繞進去了,但無可奈何。
這事兒就這麼定了。
入了夜,將離說要早睡,打發了雙慶後偷偷溜了出去。
李承昊的住處與她的相隔不遠。
剛走半道兒遇見玄暉,瞧見她就疾步上前,“大人,正找您呢。”
將離見他就一個人,預感不妙,“那姑娘呢?”
玄暉懊惱:“半道被二皇子截胡了。”
這個細狗真以為李承昊看上了這個舞姬,又不知從哪裏聽到了些風言風語,非要觸他黴頭,搶他的人。
將離頭大:“李承昊呢?”
“爺被舒王他們拖住了,非要帶他看什麼好東西。”玄暉攤手,也不知道什麼東西這麼好看,李承昊讓他先把人帶回去,這下辦砸了,回頭得挨削了。
將離搖頭,這幫紈絝子弟成日不幹正事,又不知弄出什麼花樣了。
“二皇子把人帶去哪裏了?我去找。”
“後山湯池。”玄暉有些不放心,“大人,我同您一起去吧。”
“不必,找她問幾句話,人多反倒惹人懷疑。”
湯池是將離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下了水一切無處遁形,縱然今日同僚三番四次相請,她總以不便推拒。但今晚沒轍,不得不去。
聲東擊西調開洞口守衛,將離偷偷溜了進去。湯池內鶯歌細語,侍女身子曼妙,各個都穿得很少,滿洞氤氳著天然湯泉的熱氣。
想找二皇子不難,洞口大老遠都聽到他猥瑣的浪笑聲。
將離看到一個身著輕紗的舞姬半跪著身子,另一個侍女高傲地將木盤遞給她:“你就是彩芝?能伺候皇子是你三輩子修來的福分。仔細著,惹怒主子可沒你好果子吃。”
“是。”彩芝低眉順眼地接過木盤。
盤中有一樽酒,想來是端給二皇子的。
侍女走後,將離想靠近,但奈何又有幾個侍女從旁經過,她隻能眼睜睜看著彩芝端著酒盞走入輕紗幔帳圍起來的湯池裏去。
透過燭火搖曳的紗簾,二皇子赤裸著大半個身子泡在湯池中,皮包骨頭,瘦骨嶙峋。大手勾著彩芝的脖子,色眯眯地笑,手還不老實地摸來摸去。
“李承昊這個人不行,眼光倒是不錯,美人,他不過是雀都的一條狗,哪有跟著本王好。今夜你服侍得好,明日我就將你帶回府,榮華富貴享用不盡。”
“謝殿下。”彩芝端著酒遞到他的唇邊,他一飲而盡後扣住彩芝的腦袋,與她親吻。
將離忍不住合上眼睛。嘖嘖。
心說皇家畫餅技術真是祖傳,個頂個的強。
突然,二皇子像是被鎖住了喉嚨:“你,你給我喝的什麼東西?”
“去死吧!”彩芝不知從何處摸出一把匕首,朝著二皇子都捅過去,二皇子嚇得一趔趄向湯池中仰頭摔了過去。
將離一聽不對,怎麼剛親上嘴就殺起人了?
劇本是這麼演的嗎?
她掀開布幔衝過去擰住彩芝的手,“住手!”
彩芝掙脫她,力氣很大,將離腳下一滑摔進了湯池。
“別攔著我!他殺我相公,我要他償命!”
二皇子摸著脖子哼哧哼哧喘著粗氣,在水中迷迷糊糊,彩芝手中的刀一飛,紮進他的手臂,他暈了過去。
水池一片殷紅。
彩芝欲撲過去再殺,將離拉住她,“葉小東不是他殺的。”
彩芝一臉狐疑:“你怎麼知道?”
將離耐著性子將那夜情況告之彩芝,又道:“將正言是我爹,我不會騙你。葉小東的信在哪?你交給我,我一定會查出背後真凶的。”
彩芝淌著淚:“大人,我與東哥雖然沒有明媒正娶,可我們拜過天地就是夫妻了。他和我說過,隻以為是換了封信罷了,並不知道會害死太傅。他真的是無心的,求大人寬恕他。”
“你起來吧!”將離歎了口氣,“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他的錯,我並沒有寬恕的資格。家父與他在黃泉路上相遇,自有分說。此事牽連甚多,你不要走入歧路,快走!”
“多謝大人!”彩芝抽了抽鼻子,從腰帶裏抽出一封薄薄的信遞給將離,“這信我日日帶在身上,本就想趁著避暑找到太傅之子。今日交給大人我就放心了。請務必查出幕後真凶。”
將離極其鄭重地揣進袖中,又從湯池裏像拉死狗一樣把二皇子拖出來:“好。你給二皇子吃了什麼?”
“是蒙汗藥。”彩芝麵色微紅,“我想殺他,可又怕力氣不夠,就在酒中放了藥。”
將離鬆了一口氣,好在沒毒死細狗。
“走,我先帶你出去。”
她拉著彩芝貼著洞壁,躲過侍衛和婢女,慢慢摸出洞口。
彩芝剛要行禮道謝,突然麵色一凜,鮮血噴湧而出,“大人……”
她的胸口不知何時被飛箭刺穿,汩汩流血。
“彩芝!”懷中的人怎麼也喚不醒了,身體頹然倒下,逐漸冰冷,再沒有聲息。
淩空又有幾隻飛弩射來,幾乎擦著將離的耳朵飛過,刺入她身後的樹幹上。
一道黑影撲過來,把將離卷在身下,是李承昊。
他抱住將離順勢從斜坡往下滾,飛箭如雨點落下。
他摟著將離飛速躍上一顆大樹,躺倒在枝椏之間,隱沒在黑暗裏。
急促地腳步聲自遠而近,顯然,不是一個人。
他們步履輕,氣息穩,明晃晃的劍尖還淌著血,沿著四周走來走去。
李承昊:“我去會會。”
將離伸手捂住他的嘴,低聲:“不可。”
聽氣息這些人全都是武功高強的殺手,人數眾多,貿然出手是下策。
“那你別動。”李承昊幾乎是咬著牙,身子繃得筆直,像一塊燒紅的烙鐵。
將離趴在他的身上,她臉通紅,“你別動。”
李承昊粗喘著氣,煎熬著,懊惱著。
將不棄怎麼毫無反應?
這讓他覺得敗了下風,惱上加惱。
腳步聲朝著大樹而來,李承昊的氣息越加急促。
慌亂中,將離臉靠近他。
世界靜止,惟有心跳怦怦,像是歡騰的小鹿要躍出胸口。
李承昊全身燥得幾乎要爆炸了。
該死的將不棄,該死的……
他的大手恨恨地押著她的背,將她進一步扣向自己。
將離的耳朵一直聽著外頭的動靜,見腳步聲遠離後,鬆了一口氣。
她趴著從他身上向後退,手一寸寸從胸膛、腹部、大腿根直至小腿壓過,悄然退到枝椏另一側,垂眼偷偷向下看,“可以了。”
將離一躍而下,李承昊稀稀索索地磨蹭許久,才跳了下來。
滿臉慍色,像是和天地結了不共戴天之仇,“是誰幹的!”
將離攥著拳頭搖頭,滿腦子都是彩芝中箭的畫麵,自責地無以複加。
她就在身旁,若是警醒一點,明明可以保護彩芝的。
突然,天光發紅,湯池傳來驚呼,尖叫聲刺破天際:“出事了,二皇子被刺殺了!”
與此同時,巡防的禁軍腳步紛至遝來,有刀兵相接的金屬碰撞聲。
不遠處的垂雲大殿火光衝天,亭台樓閣搖搖欲墜,已有倒塌之勢。敲鑼打鼓、奔走呼救聲響徹雲霄:“走水了!走水了!”
兩人神色大變,異口同聲:“你幹的?”
“不是我!”又是異口同聲。
垂雲大殿裏住的是皇帝。
“要出事!”李承昊雙手按住她雙肩,神色凝重,“你快回去,別出來。”
“一起。”將離沒猶豫,直接拉著他朝垂雲大殿奔去。
他們本要借著避暑將湯憲督辦的豆腐渣工程弄出點小動靜,整治這把捅人的刀子,可這一出顯然不是他們籌備的戲碼。
難道是有人趁機想發動宮變?
太子呢?太子在何處?
一路上氣氛不對,如此之大的動靜,沿路竟沒有半個巡邏的侍衛兵。
越靠近大殿,血腥味越濃,李承昊打了個哨,霄淩空一躍落在他的肩頭,他拔劍而出,利刃閃著寒光。
將離從地上的侍衛兵屍體旁撿起一把劍,跟了上去。
大殿之外的空地上,好些個官眷、內侍被十來個黑衣人刀抵著脖頸,捆押成一團,殿中火光衝天,黑燼如濃雲。
李承昊大喝:“禁軍總督在此,何人敢造反!”
內侍潘德海見到李承昊二人,哭喪著臉:“陛下還在裏頭啊!”
十多個黑衣人將兩人團團圍住,將離一襲白衣,李承昊則是黑色箭袖,一黑一白兩道身影被圍在正中,像極了太極八卦陣眼。
一聲怒吼,如陣法啟動,黑衣人默契地朝二人殺來;
兩人配合默契,劍如遊龍、氣如虹練,隻殺得酣暢淋漓,海東青時而躍下啄人眼珠子助陣,很快,黑衣人紛紛倒在血泊之中。
玄暉帶著禁軍巡防營的人及時趕了過來:“總督,出事了,碼頭守衛盡數被斬殺,一群不明身份殺手不知何時偷偷上島,與咱們巡防營兄弟殺成一團。負責安防的殿前司指揮使衛子廊大人不見了!”
潘德海被解開束縛,屁滾尿流地朝大殿奔去:“陛下,陛下,老奴隨你去了吧!”
李承昊淬了口唾沫,“禁軍何在!”
“速速布防,遇亂黨抵抗,一律格殺勿論!”
“是!”玄暉帶人匆匆而去,李承昊脫下幾個大臣的外袍,用荷花缸的水沾濕,頂著濕衣朝著頹然將傾的大殿衝了進去。
“李承昊!”將離驚得跺腳。
燒成這樣,皇帝救出來也都是塊炭了。
這不是天遂人願麼,皇帝老兒一死,太子登基,皆大歡喜啊!
這李承昊,真多事。
將離氣得咬牙,也顧不得尊卑等級了,對著地上的工部尚書文若承道:“快去找太子!”
文若承嚇得腿都軟了,連滾帶爬:“是!是!”
將離隨手打濕外袍也衝進大殿,文若承傻眼了:“侍郎,裏頭都燒沒了啊!”
濃煙滾滾,房梁不停有燃火的木頭落下,將離根本看不清裏頭的情況,更找不到李承昊的身影。
“長煦!”“長煦!”“咳咳……”
李承昊聲音飄渺:“我在這,快,來搭把手!”
將離揮開濃煙,驚喜地朝聲音的望去,笑容一滯。
李承昊正在抬一塊巨大的木柱,木頭下壓著奄奄一息的皇帝。
喲,命夠硬的,還沒死呢。
將離隻好同他一起用力抬起木柱,皇帝被壓著的那條腿已經血肉模糊。
李承昊將皇帝扛在背上,沒好氣地罵她:“你傻啊,跑進來做什麼?”
“還不是因為你,傻子。”將離更沒好氣,將濕潤的衣服蓋在皇帝頭上,兩人一起向外跑。
大殿的屋頂都燒穿了,燃火的木頭如星雨落下,兩人費了好大一番功夫才跑到殿外的空地,臉上全都是黑色的灰燼。
李承昊放下皇帝,潘德海連滾帶爬衝了過來,“陛下,陛下!快,快喊太醫啊!”
皇城司使謝世忠帶人一路廝殺前來護駕:“臣該死!臣救駕來遲!”
皇帝醒了,濃煙嗆得他直咳嗽。
“我去前方……”
李承昊扭過頭,差點站不住腳。
將離站在熊熊燃燒的大殿前,臉都是黑灰,惟有一雙眼睛映著天光大火如星辰璀璨;她唇角微微一勾,時光之河如瀑瀉流,一發不可收拾。
李承昊的腳生了根,疑問、詫異、驚喜、惶恐頃刻從全身爬出藤蔓,死死地捆住他,無法動彈。
將離隻覺得他表情有些古怪,可她沒忘記自己是帝師,當務之急要找到太子。
皇帝要是有個三長兩短的,太子必須在眼跟前才行。
“我去找太子!”她不等李承昊說什麼,轉身持劍朝太子下榻的流星閣奔去。
李承昊想追,玄暉來稟:“總督,亂黨全部拿下!領頭的正是衛子廊。”
衛子廊是貴妃的親弟弟,二皇子的舅舅。
李承昊冷下眸子,“綁起來,聽候陛下發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