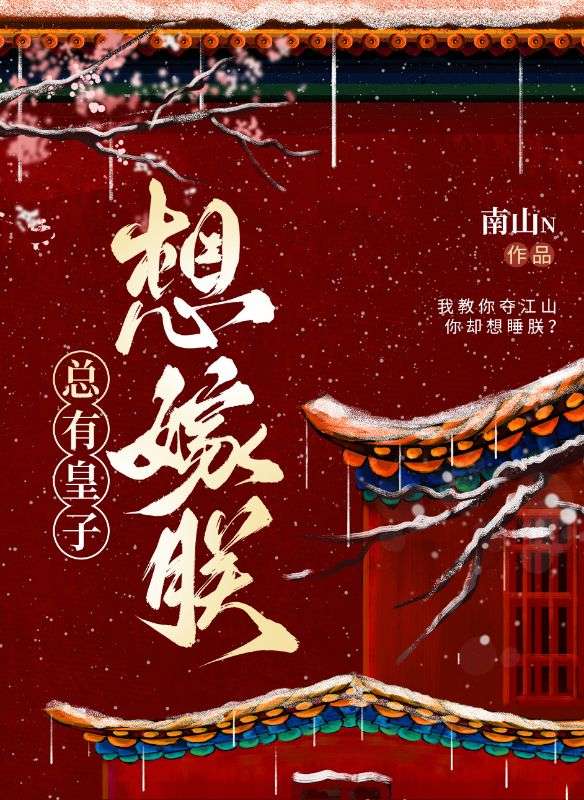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25章
保護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慧修摸了摸她的頭,開始回憶起往事。
她並不屬於這個朝代,隻知道自己醒來時,已經在這具身體裏。一開始她很不適應,鬧出不少笑話,機緣巧合之下遇到了年輕時的將正言。
那時他正輔佐當今皇帝爭天下,而紀雲茵正是皇帝的青梅竹馬。
“紀雲茵出身將門,是馬背上的女將軍,容貌更是一等一的好看;她妹妹叫紀雲齊,同李長白是一對。”慧修輕歎,“當年紀雲茵和皇帝在一起,可是吃了不少苦頭的。”
皇帝出生卑微,是先帝第三子,生母隻是個避暑山莊看園子的宮婢。先帝飲醉了酒偶然寵幸後有孕,生下了他。
“是芙蓉山莊?”將離想起那些宮中流言。
“是的。皇帝的生母很快就死了,死因不明。他一直被遺忘在孤島上,直到七歲時才被先帝想起,接回了宮中。後來在太學認識了你爹。先帝七子,你爹獨獨就相中了他,一心扶持他登上帝位。儲君之位遍布荊棘,欲殺他而後快的人多如牛毛,紀雲茵為了保護他還差點丟了性命呢。隻可惜啊,功成名就後,蕭家、謝家捏著先帝遺詔,太後逼他娶謝氏女為後。紀雲茵是個有骨氣的,絕不肯與人共侍一夫,就離開雀都去了北冥。”
將離手撐著腮,“可她不是又嫁給了北冥王李長白,與紀雲齊共侍一夫嗎?”
“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但後來我同你爹……”慧修頓了頓,“我同你爹斷了來往,也就不摻和這些俗事了。”
“柳翠筠給爹下了藥,爹並沒有背叛您,您為什麼不肯原諒他呢?”將離有些惋惜,如果慧修同將正言在一起該多好啊,她就不會是活在陰溝裏的老鼠了。
“傻孩子,我從來都沒有恨過太傅。”
慧修端起藥碗,舀了一勺進嘴裏,苦澀在唇齒蔓延,她皺了皺眉:“是這個朝代對女子太苛刻了。柳翠筠經此一遭若不能嫁給將正言,她就隻有死路一條。”
將離抬起眼,有些詫異:“您竟然是為了保護她?”
“在我們那個年代,男男女女在一起,不合適就分開,很常見,誰也不會說什麼。可這個朝代不行,女子在家從父、嫁人從夫、夫死從子,名節就是懸在她們脖子上的利刃。我若踏著她的屍體嫁給將正言,日後也不會過得安心。”
將離唏噓,她成全了柳翠筠,可柳翠筠恨了她一輩子。
“您後悔嗎?”
“不後悔。”
“可您因此出家,難道不是傷透了心?”
慧修大笑:“並不是。而是這年代隻有道姑最自在。沒什麼男女大防、人倫綱常。”
“可這麼多年,您為何沒有再嫁人?”將離真的好奇,以慧修的性格,她又不是貞潔烈女型,怎麼可能為太傅守身如玉。
慧修喝了藥,放下碗,苦得咂舌:“沒法子,見過最好的,其餘都是將就。我這個人,要就是要最好的,不想將就。”
還真是為了太傅啊。將離長歎息:
“您說我爹每個月為了那點養孩子的費用同您掰扯好幾日,想來,也是想找機會同您說說話。”
“他是君子。”慧修笑著紅了眼圈,“你可知你爹最大的心願是什麼?”
將離搖頭,慧修道:“是盼著有朝一日,去我的時代看看。”
將離的眼睛跟著亮了,慧修一攤手,“我可沒轍啊,我既不知怎麼來的,也不知該怎麼回。幸而這麼多年有你,我才不寂寞。”
將離低下頭靠在她肚子上,“師父,有你真好。”
慧修摸了摸她的頭發,勸道:“我同你說這麼多,是想告訴你,你爹什麼扶持太子登基什麼為你正名,都不重要。你本就是為自己而活。倒不如丟下這醃臢的一切,同為師回雲夢穀,咱們閑雲野鶴,豈不美哉?”
將離腦袋朝她衣裳蹭了蹭,悶聲道:“我考慮考慮。”
慧修沒有提李承昊,她見識過朝野爭鬥,內心並不希望將離同權貴在一起。倒不如尋個江湖兒郎,肆意快活一生。
將離又同她說了會兒話,才告辭離開。
李承昊一直守在道觀外,斜風輕柳,君子如玉。
他同身旁的那棵大樹一樣,高大挺拔,散發著旺盛的生命力,那強健有力的臂膀,在瘋狂而偏執的夜晚,為她抵擋了一場血腥風雨。
要不然,丁長卿昨夜會死得要多難看有多難看,可不是今兒一早被人發現赤身裸體躺在豬圈這麼簡單。
將離想悄悄從側麵小路溜走,但還是被他一眼逮到。
他策馬跟上,“等等我啊。”
琉羽同玄暉打起招呼,兩人都很有眼力見地落在後頭;
李承昊拍馬來到將離身旁,斜著身子靠向她,低聲哀怨:“昨夜哭著喊我長煦哥哥,今早提起褲子就不認人了,心寒呐。”
“一晌貪歡,彼此忘了吧。”將離冷著臉覷了他一眼,“你那麼大人了,還當真?”
李承昊嘖了聲,“聽聽!昨夜你不是都驗過了,我純得很。”
“沒臉沒皮。”將離生生憋紅了臉。
“可還疼?今日你還騎馬,我給你叫輛馬車來吧。”
將離不理他,他又撓了撓頭,紅了臉:“你是不是嫌我了?我行得很。可冊子上說,初次不可太過,會傷身子。昨夜你纏著我要,不是我不想給……”
將離勒住馬,臉都快沁出血了:“你有完沒完!”
想起昨夜,她恨不得立刻調轉馬頭去弄死丁長卿這個混蛋。
五石散加上酒,昨夜的瘋狂成了今日的噩夢,此刻,她隻想和李承昊同歸於盡。
李承昊哄著她:“好好好,不生氣,不生氣。”
“是不是將不棄欺負你?他人呢?我替你教訓他。”
“不必。”將離一口回絕,大步向前離他遠遠的。
李承昊趕緊追了上來,“那姑娘的事,聽我解釋。這件事其實是同你……”
“關我屁事!”將離一甩馬鞭,疾馳而去,根本不聽李承昊解釋。
李承昊悻悻地拍馬跟了上去,“可關我事啊。我對你是認真的!”
哎,還真給這臭丫頭說中了,這未來娘子可不是好欺負的。
這是記上仇了。
都怪全布!
掐死!
總督府偷摸溜回來的全布,莫名打了一哆嗦。
將離去了孟賀嶂的住處。
他剛回京還沒有購置宅子,陛下也沒有賜居所,因而暫居在驛館裏。
昨日昏厥後,今日頭發白了大半,人瞬間蒼老了。
“孟大人,節哀。”將離躬身拱手,甚是哀戚。
李承昊這個黏皮糖也跟過來了,客氣地拱了拱手。
“兩位大人,有心了。”
孟賀嶂有氣無力地應著,但坐姿還是非常板正,依稀能見到當年的風骨。
將離開門見山:“本不該來叨擾孟大人,實是心中有諸多疑團,還盼大人能解惑。”
孟大人頷首:“尚書大人,請問,下官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您說親眼見到我父親寫信,可據我所知,我父書寫密信從不當人麵的。”將離直視他的眼睛,“您撒謊了。”
孟賀嶂竟爽快地承認了:“是。我的確沒親眼看到過信,可出事後我聽了信中內容,就斷定北冥王手中的信是假的。因為信上沒有提葉州私煉鐵一事。”
將離與李承昊對望了一眼,“您是說,我父親知道葉州煉鐵?”
“慚愧,這件事是我告訴恩師的。屠光在葉州的勢力盤根錯節,恩師叮囑我切莫張揚,他先附信告之北冥王,以期暗中查實後再一舉將屠光捕獲。可北冥王在朝廷的邸報中並未提及此事,我便知道這其中另有內情。”
他看向李承昊:“恕我無禮,我並不知道北冥在其中是否有牽扯,因而……”
李承昊了然,孟賀嶂不信北冥。
“你懷疑北冥同葉州屠光有勾結。”
孟賀嶂起立拱手:“多有得罪,下官願負荊親至北冥請罪。”
李承昊看了一眼將離,從前他有多怨恨孟賀嶂,現在就有多感激他;要不是他咬死了信有問題,他還未必能入雀都為質,也找不著將離了。
因而他心情很好,一片雲淡風輕:“無妨,都是為了朝廷嘛。”
孟賀嶂也不知道他是真無妨還是假陰陽,隻訕訕地落座,看向將離:
“尚書大人,太傅死前葉州城曾有疑似錫人出入,我懷疑,使團路線是屠光泄的密,他是有預謀要殺太傅,讓北境戰火重啟,牽製北冥,他就可以伺機造反了!”
將離和李承昊頷首,如今看,正是如此。
“孟大人,家父在雀都還有個小宅子,您入京前已吩咐人收拾了,過兩日待您身體好些,就讓府中下人來幫您搬過去吧。這是房契,請務必收下。”將離從袖口掏出一份契書,早在孟賀嶂進京前將不棄就命她著手去辦了。
“使不得,使不得!下官怎可收如此重禮。”孟賀嶂連連推卻。
將離在初次見麵就打量過他的衣著,官袍、鞋靴都洗的發白,聽聞他被屠光打壓,連葬老母的銀錢都是問人借的,可想而知經濟有多拮據。
“您就不要再推辭了。否則,太傅在天上也要怪罪將大人的。”李承昊最不喜推來推去的,直接奪過房契塞進了孟賀嶂的手裏。
他一揚手,玄暉又掏出幾張銀票遞了上去。
“這是本世子謝你的,一並收了。”
這回輪到孟賀嶂呆若木雞了,因著他的供詞將北冥牽連進太傅之死,這位世子才會被困在雀都為質,怎麼還謝上他了?
“愣著做什麼,快收了。你可是本世子大恩人。”
他起身拍了拍孟賀嶂瘦削的肩膀,又拉上將離,“天都黑了,別耽誤孟大人養病。”
將離被他拖著往外走,“哎,你放手。”
“不放。”大男人耍起賴皮了。
將離一怒:“李承昊!”
李承昊嗖地鬆開:“好好好,別動氣嘛。”
孟賀嶂在屋內看傻了眼:“這尚書大人和李世子這般要好?”
驛丞也鬧不明白:“聽說前兒兩人還打過架呢。”
出了驛館,華燈初上。
這條街市是雀都最熱鬧繁華的地段,沿路兩側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攤位,商販叫賣聲此起彼伏,兩側酒樓瓦肆鱗次櫛比,布幌搖曳。
“餓了吧?爺帶你去吃東西,好不好?”李承昊舔著臉問。
將離懶得理她,招呼琉羽就往前走,“不必。”
“別啊。餓肚子怎麼成?馬上入冬了,紅燜羊肉最合時宜,越西樓的廚子是涼州來的,做得特地道。我每年來雀都必吃的。”
不提這茬也就罷了,將離嗤了聲,“總督有此雅興,應該帶貴府星星姑娘去吃。我就不湊這個熱鬧了。”
“同她有什麼關係。我隻想同你去吃。”
這個臭不要臉的東西,將離心梗,“琉羽,我們走!”
琉羽踟躕不前,肚子不爭氣地咕嚕咕嚕叫著,玄暉低頭悶笑,李承昊可算找到由頭了:“小丫頭都餓壞了。你扛餓,她不扛餓啊。琉羽,那越西樓最好吃的可不是這紅燜羊肉,你想知道是什麼嗎?”
琉羽的口水都下來了:“是什麼?”
“是芙蓉花奶酪酥。你想想啊,大雪紛飛,炭盆烤著羊肉,滋滋冒油;你一口羊肉,一口冰奶酪,嘖,那真是冰火兩重天,賽過活神仙呐!”
琉羽舔著唇,吞了吞口水,開始走不動道兒了。
“大人……”她可憐兮兮地摸了摸肚子,將離被打敗了,恨恨地剜了一眼李承昊。
李承昊順勢就讓玄暉拉走她手裏的馬,拽著她的手往越西樓走。
“就在前頭不遠,咱們走著去就行。”
路上行人摩肩接踵,將離試圖甩開他的手:“注意分寸!”
“注意什麼注意!”李承昊反握得更緊,聲音提得高高的,“勞資就是龍陽,怎麼了?”
行人目光聚焦到兩人的手上,吃吃暗笑;將離臉緋紅如血,“你玩夠了沒!”
“當然沒夠!將不棄這個死玩意欺負你,我就要把他的名聲搞臭!”
一句話惹得將離又撲哧笑出了聲。
“笑了?”李承昊心都化了,“可算是笑了。”
“那你的名聲,不是一起臭了?”將離看著他。
“名聲有什麼用?又不能當飯吃!”
他的大手順著手肘滑下與她十指相纏,握得緊緊的,歡喜滿得要溢出來。
手心的薄繭輕輕地摩擦著,帶著絲絲縷縷的心悸,兩人都忍不住低下頭。
周邊有人經過,竊竊私語。
“看,那兩男人牽著手呢。”
“真不要臉,這光天化日的。”
“你瞧瞧,世風日下,都不避人了。”
李承昊氣沉丹田,像一直驕傲的鬥雞,見人就噴:“沒錯!我就是斷袖!”
“肥婆,關你屁事!爺就愛男人!怎麼滴了!”
他凶神惡煞的樣子嚇壞了嚼舌根的肥婆娘,人一人竹籃筐,撒丫子就跑。
有好事者已經認出了兩人的身份,嘰嘰喳喳地交頭接耳,傳得更凶了。
雖說汙的是將不棄的名聲,可將離還是尷尬得想鑽地洞。
“差不多得了,李承昊。”
李承昊手肘與她輕撞,低頭湊至她耳根:“聽娘子的。”
噗……將離差點噴出一口老血。
“你閉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