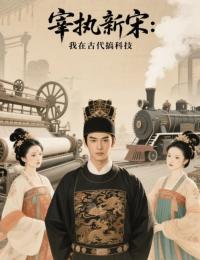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7章
紫宸殿前的漢白玉台階在晨光中泛著冷冽的光澤,淩泉跟在引路太監身後,靴底與石階相觸發出輕微的"嗒嗒"聲。他懷裏抱著個一尺見方的木匣,匣中是他熬了七個通宵製成的邊城防禦模型。每走一步,匣中的零件就輕微碰撞,像他此刻忐忑的心跳。
"候著。"太監尖細的嗓音刺得人耳膜生疼,指了指殿外長廊下的一排錦凳。
淩泉謝過,小心翼翼地坐下。周圍已經候著十幾位貢士,個個錦衣華服,唯有他一身半舊的靛藍襴衫,袖口還沾著些許木屑。那些貢士們三三兩兩聚在一起談笑,目光掃過他時,眼中滿是輕蔑與好奇。
"這位可是'格物案首'?"一個穿著湖綠綢衫的貢士搖著泥金折扇走近,聲音甜得發膩,"久仰久仰。"
淩泉起身拱手:"不敢當。"
"聽聞淩兄擅製器械?"綠衫貢士湊得更近,扇子掩住半邊臉,壓低聲音道,"不知可會做...春宮機關?"
周圍爆發出一陣哄笑。淩泉麵不改色,隻是輕輕拍了拍懷中木匣:"在下隻會做些守城禦敵的粗笨物件,比不得諸位風流雅致。"
綠衫貢士討了個沒趣,訕訕退開。淩泉重新坐下,指尖摩挲著木匣邊緣——那裏刻著個小小的齒輪標記,是他每件作品必留的暗記。
殿內突然傳來淨鞭三響,緊接著是太監拖長聲調的宣召:"宣——慶曆二年貢士入殿覲見——"
貢士們立刻按會試名次排成兩列。淩泉因是"格物科"特取,排在末位。踏入大殿的瞬間,沉水香的馥鬱氣息撲麵而來,混合著墨硯的清香,莫名讓人心神一凜。
紫宸殿比想象中更為恢弘。三十六根朱漆巨柱撐起藻井,上麵繪著日月星辰的圖案。禦座設在九級台階之上,兩旁雁翅般排開兩列紫袍重臣。淩泉不敢直視天顏,隻隱約看見一抹明黃色的身影端坐在龍椅上。
"跪——"
貢士們齊刷刷跪倒。淩泉小心地將木匣放在身側,額頭觸地時,冰涼的金磚透過皮膚傳來絲絲寒意。
"起。"
淩泉抬頭,這才看清了仁宗皇帝的模樣——出乎意料地年輕,麵容清瘦,眉宇間帶著幾分倦色,但雙目卻亮如晨星,正若有所思地打量著殿中眾人。
"今歲策問,"仁宗開口,聲音不疾不徐,"朕欲聞諸生對西北邊患之策。"
禮部尚書出列,展開黃絹宣讀考題:"問:西夏猖獗,邊城屢遭侵擾,卿等有何良策..."
考題宣讀完畢,貢士們依次作答。前幾位無外乎"增兵戍邊""嚴明軍紀"之類的老生常談。淩泉注意到,每當有貢士提到"增稅以充軍餉"時,坐在右側首位的紫袍老者就會微微頷首——那人長須垂胸,麵容威嚴,想必就是權相呂夷簡。
"淩泉。"太監尖聲喚道。
淩泉深吸一口氣,抱著木匣出列:"學生有一策,請禦覽。"
殿中頓時一片嘩然。按例,殿試隻需口述對策,哪有當庭展示物件的?
"放肆!"呂夷簡果然厲聲嗬斥,"金鑾殿上,豈容匠作之事!"
淩泉不慌不忙,跪地叩首:"陛下明鑒,學生所獻非尋常玩物,乃禦邊利器。口述難盡其妙,故冒死請呈。"
一陣沉默後,仁宗竟輕輕"嗯"了一聲:"準。"
淩泉心跳如鼓,小心地打開木匣,取出裏麵的模型——那是一座微型邊城的剖麵,城牆由數十個可拆卸的模塊組成,每個模塊都標著不同顏色。
"此為學生所構'模塊化城防'。"淩泉聲音清朗,回蕩在大殿中,"城牆分九層構造,最外層為活土,可消弭炮石衝擊;中層設鐵網,防敵軍掘地道;內層用夯土夾石,堅固耐用..."
他邊說邊演示,手指輕巧地拆解著模型。城牆在他手中如同活物,時而展開露出藏兵洞,時而翻轉現出箭孔。最精妙的是城門處的機關——用絞盤帶動齒輪組,一人之力便可啟閉千斤閘門。
"各模塊預先製好,運至邊地組裝,較傳統築城省時七成。"淩泉越說越流暢,"且損毀時可快速更換,免去全軍覆沒之危。"
殿中鴉雀無聲。淩泉偷眼看去,隻見仁宗身子微微前傾,眼中閃著異樣的光彩;範仲淹捋須微笑,頻頻點頭;而呂夷簡的臉色卻陰沉得能滴出水來。
"荒謬!"呂夷簡突然拍案而起,"城牆乃國之屏障,豈能如孩童積木般兒戲!"
淩泉不卑不亢:"呂相明鑒,此非兒戲,乃學生親赴邊關所見所思。西夏攻城,常集中火力破其一點。若城牆如常製,一處破則全城危;若用此法,破損處可迅速更換,如..."
"如縫補衣裳?"呂夷簡冷笑,"軍國大事,豈容匠人妄議!"
這話說得極重,殿中氣氛驟然緊張。淩泉感到後背已經濕透,卻仍挺直腰杆:"呂相,學生鬥膽一問:邊關將士血肉之軀擋敵箭時,可會嫌棄盾牌是匠人所造?"
"大膽!"呂夷簡勃然大怒,紫袍無風自動,"陛下,此子目無尊卑,當逐出殿去!"
"呂卿且慢。"仁宗突然開口,聲音雖輕卻不容置疑,"朕倒想細觀此物。"說著竟從禦座上起身,步下丹墀。
天子近在咫尺,淩泉甚至能聞到龍袍上熏染的沉水香。他屏住呼吸,看著仁宗修長的手指輕輕撥弄模型上的小機關,城門"哢嗒"一聲開啟,露出裏麵的杠杆裝置。
"妙。"仁宗輕歎,"此物造價幾何?"
"回陛下,"淩泉聲音發緊,"較傳統城牆省料三成,省工五成。"
"陛下!"呂夷簡急步上前,"城牆乃千秋大業,豈能計較錙銖?況此等奇技淫巧,恐有違聖人之道!"
一直沉默的範仲淹突然出列:"呂相此言差矣。管子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築城安民,方為聖道。"
"範希文!"呂夷簡怒目而視,"你這是在指摘朝廷邊防不力?"
"下官不敢。"範仲淹拱手,卻寸步不讓,"隻是邊關將士浴血,我等在朝堂之上,總該為他們多備幾分勝算。"
兩位重臣劍拔弩張,殿中空氣仿佛凝固。淩泉跪在地上,額頭滲出細密的汗珠。就在這時,模型中的一個齒輪突然"哢"地卡住了——是他在緊張中碰歪了某個部件!
仁宗卻笑了:"愛卿們且看,這小機關倒像極了朕的朝堂——一個齒輪卡住,整個朝局都轉不動了。"
這玩笑話讓緊繃的氣氛稍緩。呂夷簡勉強擠出一絲笑容:"陛下聖明。隻是老臣以為,治國當以德為本,器為末..."
"呂卿,"仁宗打斷他,手指輕輕撥正那個齒輪,模型又順暢運轉起來,"朕記得當年澶淵之盟,若非床子弩震懾遼軍,恐怕..."
呂夷簡臉色一變。澶淵之盟是他的心病——當年正是他主張和議,若非寇準力主抗戰,大宋險些喪權辱國。
"陛下明鑒。"範仲淹趁機進言,"淩泉此策,實乃老臣在西北所見所聞之結晶。若蒙聖允,臣願親赴邊關督造。"
呂夷簡冷笑:"範大人這是要棄新政於不顧?"
"新政為安內,邊防為攘外,二者不可偏廢。"範仲淹聲音鏗鏘,"若呂相不棄,不妨同往?"
這話戳中了呂夷簡的軟肋——養尊處優的權相哪吃得了邊關風沙?他紫漲著臉,突然轉向淩泉:"小子,你這模型,可經得起實戰檢驗?"
淩泉深吸一口氣:"學生願親赴邊關,與將士同守第一座模塊城。"
"好!"仁宗突然拍案,"朕準了。範卿,此事由你全權督辦。"
呂夷簡眼見大勢已去,突然厲聲道:"陛下!老臣還有一問。"他死死盯著淩泉,"此等精巧機關,絕非寒門學子所能獨創。說!你是從何處偷師的?"
這一問極為毒辣,暗指淩泉通敵。殿中頓時鴉雀無聲,連仁宗都皺起了眉頭。
淩泉卻笑了:"呂相明鑒,學生確實有師承。"他從懷中掏出一本舊冊子,封麵上赫然寫著《武經總要》,"此乃家父遺物。家父生前不過一介邊關小吏,卻將畢生心血注於此書。學生所學,皆源於此。"
呂夷簡剛要再問,範仲淹突然高聲道:"陛下,此書臣亦見過,確是兵家寶典。淩泉之父淩振,當年在西北軍械司任職,因不肯同流合汙而遭貶黜,鬱鬱而終。"
這話裏有話,暗指呂夷簡一黨把持軍械采購,中飽私囊。呂夷簡勃然大怒,竟不顧朝儀,一把揪住範仲淹的衣領:"範希文!你含血噴人!"
範仲淹的進賢冠被扯落在地,發出清脆的聲響。滿朝嘩然!仁宗臉色一沉:"放肆!"
呂夷簡這才驚覺失態,慌忙跪地請罪。範仲淹卻不慌不忙地拾起冠冕,重新戴好,隻是那冠上的玉珠已經摔裂了一道細紋。
"陛下,"範仲淹平靜地說,"呂相年事已高,邊關風沙恐難承受。臣請獨往。"
仁宗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突然笑了:"二卿皆為朕之股肱,何必如此?呂卿,你既質疑此策,不如遣一心腹隨行督察?"
呂夷簡眼前一亮:"臣薦三司判官趙宗實。"
淩泉心頭一跳——趙宗實!那不正是私鹽案背後的大魚?
"準。"仁宗起身,示意退朝,"淩泉,朕期待你的捷報。"
"臣,遵旨。"淩泉深深叩首,額頭抵在冰冷的金磚上,久久沒有抬起。
退朝後,淩泉抱著模型走出紫宸殿。陽光刺得他睜不開眼,這才發現後背已經濕透。遠處,範仲淹被一群官員圍著,正說著什麼。老人頭上的進賢冠依然端正,隻是那道裂痕在陽光下格外刺眼,像一道永不愈合的傷口。
"淩公子。"一個小太監悄無聲息地湊過來,塞給他一張紙條,"範大人讓給的。"
淩泉展開紙條,上麵隻有八個字:"齒輪已轉,小心咬合。"
他抬頭望向北方,那裏是延州的方向,也是風暴的中心。手中的模型突然變得沉重無比——這不隻是一堆木頭零件,而是無數邊關將士的性命所係。
風吹過殿前的銅鈴,發出清脆的聲響。淩泉深吸一口氣,大步走向宮門。他知道,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