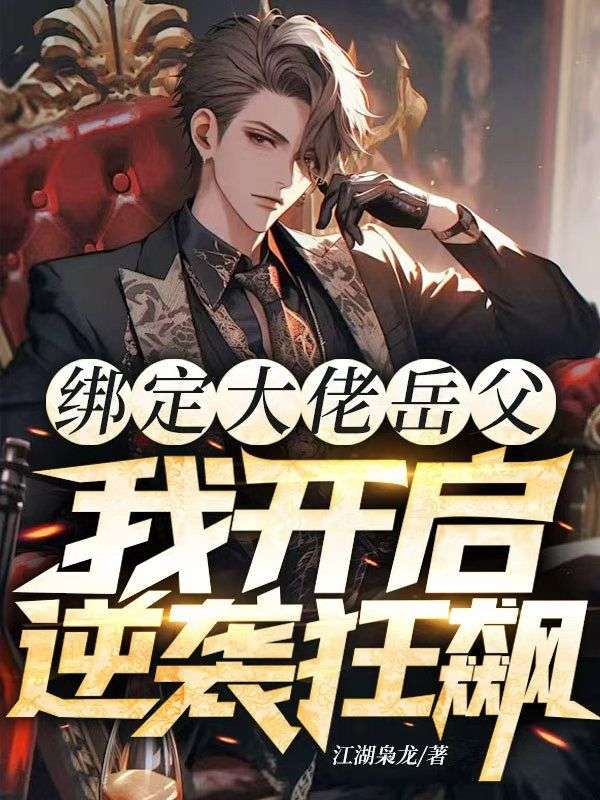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章
江湖不是打打殺殺,江湖是人情世故!
......
1997年,大年初二。
寒風卷著細雪,刮得人臉生疼。
"來根煙?"
表哥任鳴榮叼著煙,遞給任傑一根。
"我還小,不抽。"
任傑搖頭拒絕,目光卻像被磁石吸住,黏在他身上挪不開。
皮鞋鋥亮得能照見人影,嶄新的皮夾克筆挺得沒有一絲褶皺。
最紮眼的是他手腕上那塊金燦燦的表,在灰撲撲的院子裏都閃著光,渾身上下就透著倆字,
"有錢"!
任傑心裏說不出是啥滋味,又酸又脹,喉頭發緊。
1978年生在北方一個小山村,是家裏的獨苗,爹娘寵得厲害。
骨頭硬,酒量也硬!
十五歲那年,叛逆勁兒上來,死活不肯上學了。
爹娘拗不過,托二叔讓任傑在鎮上的廠子裏當童工。
二叔練過武,那拳腳功夫讓他著了迷,跟著二叔苦練三年,身子骨倒是練得結實。
廠裏一個月二三十塊錢,活兒輕鬆,可日子一眼望得到頭,任傑憋屈得慌。
前兩年,表哥任鳴榮結婚的消息傳來,還蓋起了兩層小樓,紅磚白牆,氣派得很,成了十裏八鄉的談資。
任傑知道,任鳴榮是從南方倒騰貨回來賣,賺了大錢。
他也想......他也想這樣!
賺大錢,蓋樓房,讓爹娘揚眉吐氣!
狠狠打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嘴臉。
任傑聽說表哥跑一趟,掙的錢頂他們廠子幹好幾年!
尤其母親身體不好,急需用錢。
這念頭像野草,在任傑心裏瘋長。
"你小子......"
任鳴榮沒等任傑那點羨慕在心底發酵完,就粗魯地踮腳揉亂他的頭發。
"幹啥呢?別教壞小孩子......"
一道溫柔的聲音響起,任鳴榮被輕輕推開。
表嫂穿著皮靴,裹著粉紅色的大衣,手裏提著串親戚的禮盒。
表嫂是任傑見過最美的女人。
瓜子臉,水嫩得仿佛能掐出水來,五官精致得不像話。
尤其那雙眼睛,看人時像含著水光。
身材高挑,尋常衣服穿在她身上,也顯得格外貴氣。
"小傑,長高了不少啊!"
表嫂對他笑了笑,語氣溫和。
"行了,進屋說吧。"
任鳴榮聲音平淡地打斷,率先向屋裏走去。
任傑剛才正在院子裏掃雪,並不覺得煩,瑞雪兆豐年嘛。
趕緊從表嫂手裏接過禮盒,心裏忍不住想:
表哥真是好福氣,娶了這麼好看的媳婦,還這麼有錢。
飯桌上,酒過三巡。
任傑看著任鳴榮碗裏堆成小山的肉,再看看任鳴榮手腕上那塊金表,借著酒勁,憋紅了臉開口:
"哥!帶我出去吧!跟你去南方,廠子裏那點錢,不夠塞牙縫的!我想跟你學本事,掙錢,掙大錢!"
任鳴榮端著酒杯,眯著眼看任傑,帶著幾分戲謔:"南方?那地方水深得很,可不是小孩子過家家。
喝贏我,就帶你去!"
"君子一言!"
任傑梗著脖子應戰,豁出去了!
最終,任鳴榮吐得昏天黑地。
任傑強壓著翻江倒海的胃,扶著牆,硬是沒倒。
元宵節剛過,2月22號。
任鳴榮騎著那輛村裏少見的紅色"幸福250"摩托車,突突地冒著青煙停在任傑家門口。
引擎聲震得雞飛狗跳。
"收拾一下,跟我走。"
幹脆利落。
到了任鳴榮鎮上的家,那棟讓任傑眼熱了很久的兩層小樓。
任鳴榮自己收拾了些東西,然後打開衣櫃裏一個帶鎖的抽屜。
裏麵是厚厚幾遝嶄新的"四大領袖",晃得任傑眼暈。
隨意地抽出幾遝,塞進一個看著很舊、毫不起眼的蛇皮袋裏。
那隨意的動作,仿佛塞的不是錢,而是廢紙。
趁這空檔,表嫂把任傑拉到一邊,眉頭微蹙,眼中盛滿不安:
"小傑,答應嫂子,在外麵......多看著點你哥!
那裏亂,他性子急,容易惹事......一定把他......平平安安帶回來!"
表嫂的擔憂讓任傑心裏一沉,但任鳴榮那鼓囊囊的蛇皮袋帶來的衝擊更大。
當即把胸膛拍得砰砰響:
"嫂子你放心!就算我出事,也不會讓表哥少一根汗毛!"
"都要好好的!"
表嫂嗔怪一聲,沒再多說。
不多時,任鳴榮收拾妥當,兩人坐上了去火車站的大巴。
車啟動時,任傑從車窗望出去。
表嫂站在小樓門口的身影越來越小,那份不安似乎也隨著距離拉長了。
車上顛簸。
"喏,來一口?"
任鳴榮用腿緊夾蛇皮袋口,把點燃的煙遞給任傑。
任傑搖搖頭:"真抽不來。"
"以後學著點,這玩意兒有時候比拳頭好使。"
任鳴榮意味深長地說了句,沒再勉強。
上了火車,一切都讓任傑感到新奇。
鐵疙瘩跑得這麼快,車廂裏人聲嘈雜,絲毫沒減弱任傑的興致。
看了幾個小時的窗外風景,單調的景色終於催生了睡意,他不知不覺就睡著了。
再醒來,任傑是被任鳴榮推醒的。
"走了,到了。"
跟著任鳴榮擠出火車站,這一覺竟睡了十幾個小時。
任鳴榮讓他換上帶來的舊短袖,不然真得熱壞。
老家那邊還冷得夠嗆,這裏卻溫暖得如同初夏。
空氣裏都帶著股潮濕的、陌生的味道。
人潮洶湧,高樓林立,看得任傑眼花繚亂。
好不容易擠出人潮,找了個稍微僻靜的角落。
任鳴榮讓他原地守著行李。
蛇皮袋沒讓任傑碰,似乎有些防備,也可能怕他年輕露了財。
任鳴榮自己則走向不遠處一個賣水和香煙的小攤販。
站外,不少摩托車在拉客,那時正是摩托車的黃金年代,便宜又方便。
真是亂花漸欲迷人眼!
任傑正新奇地打量著這光怪陸離的南方城市。
一個穿著牛仔褲、花格子襯衫、身材高挑的姑娘進入他的視野。
她的視線,最終牢牢鎖定在任鳴榮身上。
尤其是在任鳴榮緊緊護著的那個不起眼的蛇皮袋上停留了好幾秒,眼神裏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精光。
然後,她嘴角勾起一絲若有若無的笑意,整理了下衣衫,徑直向他這個方向走來。
任傑心裏頓時警覺:壞了,這女的想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