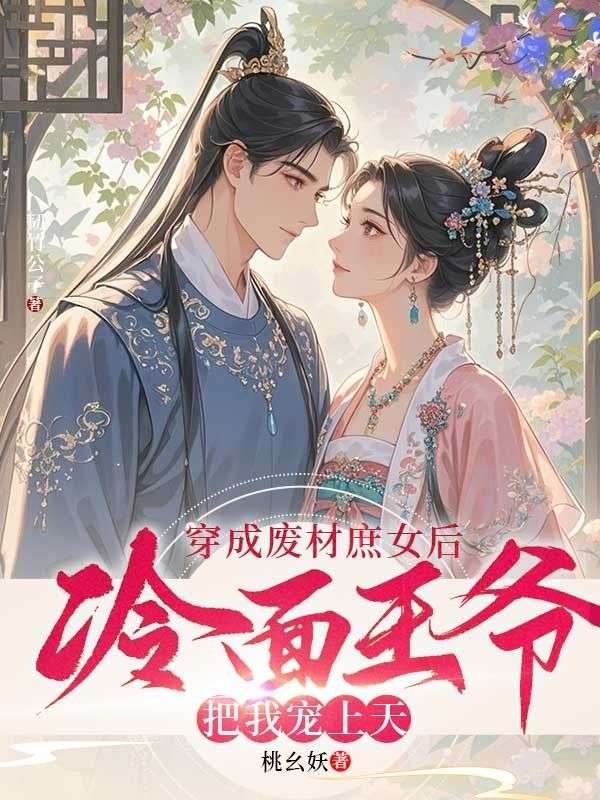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10章
包裹裏隻剩下兩個幹硬的饅頭,莊黎沒舍得吃,給了趕車的鄭伯一個,青釉和李良笑各半個,結果青釉發燒也沒有胃口,連哄帶騙的隻喝下幾口水,腦袋卻越發燙起來。
莊黎有點著急了“鄭伯,天黑前我們別忙著趕路了,找個鎮子給青釉揀點藥要緊!”
她把那錠金子放在懷裏,待會就帶到城裏去,找個錢莊兌換了,身上已經沒有盤纏給青釉請大夫。
這裏已經離甘肅不遠了,四麵都是連綿不絕的群山,山路越發難走,彎彎繞繞,路又濕滑,這老破車虧得鄭伯幾十年的好手藝,要是個年輕些的車夫,非得打滑到懸崖下去。
越是這種地方呆久了,莊黎隱隱覺得不安,這幾日路過的城鎮,已經是民生凋敝,盜搶猖獗,一路上已經遇到了好幾撥盜賊,青釉病著,得趕緊找大夫,多生些事端就慘了
“姐姐,別怕,不是還有我呢!”那李良笑倒還貼心,一邊亮出了自己瘦小的胳膊上麵姑且算他有一個小小的突起,據他所說是肌肉。莊黎哭笑不得。
那李良孝卻越發認真起來,
“姐姐,你不要太操心,我要飯也能養活姐姐的!”
莊黎一驚,沒想到他說出這樣的話,心裏一陣暖,又覺得這小小的孩子怎麼總惦記著要飯呢,趕忙教他
“你還小,除了要飯還有許多事情可做啊,要習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懂嗎?到了甘肅給你找個先生好好念書,不要再提要飯了!”
行到傍晚總算遇著個鎮子,兩條街道,莊黎先安頓好青釉在一個破舊的小客棧躺下,讓鄭伯照顧好青釉和馬,就帶著李良笑去錢莊兌換金子。
街上人不多,莊黎將兌換好的銀票放在身上,趕緊去鎮裏找大夫給青釉看病。路上遇到一些人奇怪的盯著她看,李良笑就拉著她的手,跑得飛快。
直到大夫過來,開了藥,煎了給青釉服下,莊黎這才微微放寬了心,那孩子燒得糊裏糊塗,睡夢中一會兒喊娘親,一會兒喊小姐。聽著心疼。
他們開了兩間屋子,青釉和莊黎住一間,鄭伯和李良笑住一間,一旦放鬆下來,莊黎便覺得自己也疲憊得幾乎都要站不穩了,顧了會青釉的情況,還算穩定,就倒在青釉邊上,連睡衣也懶得換就這樣睡著了。
不知道過了多久,莊黎隱約感覺到有什麼在晃動她,她剛睜開眼想說話就有一隻手捂在了她的嘴巴上
“怎......”
然後一個毛乎乎的腦袋湊到她耳邊極為小聲的說了句
“姐姐,是我。”
李良笑?莊黎已然清醒了大半,她趕緊睜開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房間窗外的煙火和人影,然後是一些哭喊和吵鬧聲。
這......這......是遇上山匪了!?
莊黎趕緊轉身把青釉抱起來在懷裏,這孩子晚間喝了藥,呼吸剛平穩些,身體卻還燙著,虛軟無力的搭在莊黎身上,就見李良笑靈活得像個小動物一樣又翻身到窗口看了一下外麵的情況。
她們住的,是這客棧小樓的第二層最裏間,大概是那土匪忽略了這個角落,莊黎她們才得以躲過一劫,李良笑摸回來,拉著莊黎給她指了指屋後的一塊半斜開的窗子,大約剛才李良笑聽到動靜,就是從這窗口爬過來,給莊黎報信的。
那鄭伯怎樣了?
李良笑隻是搖頭,催著莊黎快走不要管,莊黎心跳撲通撲通的,就聽到院外鄭伯的哀求聲
“不要,不要殺我的馬!”接著是一片成年男人的哄笑聲,夾雜著些許婦女的哭聲。
“我沒有錢了,逃難道這裏的,官爺,官爺你放過我!”
“臭娘們,還有幾分摸樣,土胖子,裝到你車上去!”
然後估計著那婦女就被拉上車,聽著他丈夫無助的哭喊,接著又是錘打聲,又是女人悲痛的哭喊聲,嗚哇哇的亂做一團。
莊黎收拾好包裹,慌亂中將青釉扶到自己背上,可她也已經是舟車勞頓,饑一頓飽一頓,腳步虛無,沒走幾步,就絆倒在地上。
李良笑趕緊把青釉拉起來,他個子小小瘦瘦,勉強抱起青釉,卻也打著晃兒,催促莊黎快走。
“二樓,二樓角落裏,怎麼還有間房關著?”
原來那土匪先是將屋子裏的人全部趕出來集中在院子裏,現在就他們這間屋子的門關著,自然顯得突兀起來。
莊黎嚇得手心一緊,更快的把青釉接過來,讓李良笑先翻出去,好在外麵接著青釉。
門外已經傳來了山匪逼近的腳步聲。
李良笑在窗外接過青釉,又拉出莊黎來,窗外隻是個窄小的過道,莊黎蹲在地上哆嗦,就在這時後,見李良笑又極為靈敏的爬起來從窗口翻進去。
莊黎一把拉住他,著急的差點哭出來“你幹什麼!”
那李良笑隻是也抓住她的手,那雙小手熱乎乎的,比起莊黎冰涼冰涼的手顯得格外溫暖,他用力握了一下莊黎的手掌,好像想在這一瞬間將熱量全部傳導到她的身體裏。
借著月光,莊黎看到李良笑那張小臉,之前如同小動物的雙眼撲閃撲閃的現在卻是透著一股執著與堅定。他張開嘴巴,微不可聞的說了句:“姐姐,你放心。”就放開莊黎的手,嘩的縮回屋內,並且關上了窗子。
然後就聽到土匪猛的推開門,他們舉著火把,瞬間將屋內照得明明晃晃。大約是一個土匪率先衝到窗前,摸了一下被子。
“大哥,還是熱的,人跑了!”接著是踹翻桌子的聲音。
土匪很快注意到屋後的窗戶,走過來一把扯開窗簾,而他先看到的,則是蹲在地上的李良笑。
“這個房間就住你一個人?”
“我跟外人睡不好,都是一個人睡!”
“穿得這樣,窮人家的孩子,講究還挺多?”
那土匪約莫是將李良笑擰了起來,在火光下仔細看“長得倒還水靈,可以賣到勾欄院裏做兔兒爺......”
一片哈哈哈的哄笑聲。莊黎就蹲在隔著一層紙的窗外,握著拳頭,她沒有意識到指甲已經把手掌穿透,整個拳頭都是血,而自己已經淚流滿麵。
她控製不住自己不斷的發抖,那雙手剛剛被李良笑握過,那個孩子暖暖的好像小太陽,他說。
“姐姐放心。”
“姐姐不要怕。”
莊黎想進去好好把那個孩子抱在懷裏,那如果自己出事了,病得糊裏糊塗的青釉又怎麼辦呢?
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在這個世界的弱小,不是自己糊裏糊塗就混得下去的小生活。
她以為自己的生活如透明的水晶一樣漂亮的杯子,卻被輕輕一敲,就破碎得體無完膚。
“小姐......”
莊黎聽見青釉的夢囈迷迷糊糊的醒來,已經喜歡性的用手去探她的額頭。然後總算歎出一口氣。
“總算退燒了。”
自前幾日劫匪過後莊黎也帶不動青釉,就在在劫後的院子住下來,按時將大夫開的藥熬給青釉喝,青釉漸漸好起來,清醒時候哭了幾場,問莊黎那日的情況。
莊黎不想再提,也不言語,還是安慰青釉沒有關係。
那日就這樣李良笑和鄭伯還有客棧一幹人等都被土匪帶走了,莊黎打聽過,這裏已經是靠近西域,本來就不太平,西域的匪徒也經常過來騷擾,這群山匪也長期來這鎮上打劫,所以這鎮子怎麼也富不起來,劫錢劫色,將人賣到磚窯做苦役年輕漂亮的婦女就賣到勾欄院裏去,這地方山高皇帝遠,主縣城也在相隔幾十裏的山外,山匪犯了事官差都要大半天才能趕到現場,山匪則是腳底抹油往山裏一鑽,什麼事都沒有了。
久而久之縣太爺也不管了,自然也就沒有人再報案了。
莊黎聽得淚眼婆娑,一麵加緊照顧青釉,一麵打聽甘肅的方向,這個地方不宜久留,若是鄭伯和李良笑逃出來,定會去甘肅老家等她。青釉一病好了馬上就出發,她得給自己找到某個盼頭,讓自己再撐著走下去。
“小姐,你喝點粥吧!“青釉把粥放在莊黎手上。
“嗯”!莊黎應了一聲,端起來喝了一口,青釉恢複得不錯,看來明兒一早就可以繼續啟程了。
客棧的小破院傳來了一片馬蹄聲,莊黎經過那日的事已經是心頭一緊,趕緊從窗口往外張望,一群人馬也皆是凶神惡煞的衝進來,那小破院的老板已經是哭著跪倒在院裏。
“爺爺啊,你放過小的吧!我這小院前幾日才被山匪打劫過!現今是連個銅子兒都收不出來啦,實在無能為力孝敬爺爺啊!”
莊黎是被人當頭一棒,這特麼不是剛出狼窩又入虎口麼!
那為首的大漢哪管那店家說些什麼,一腳就將他踹飛出去,便呼著手下進屋收刮,莊黎先是一驚,接著卻冷靜下來,緊緊握住青釉怕得發抖的手,她一抬頭就看見當日李良笑將她們藏起來的小窗口。
“快,快走!”她將青釉推到那窗口,慌亂的交代著“快爬上去,躲在裏麵不要出聲!”
青釉淚痕斑駁,想拉住莊黎,卻沒料到莊黎死命的掙脫,門卻嘩的被踹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