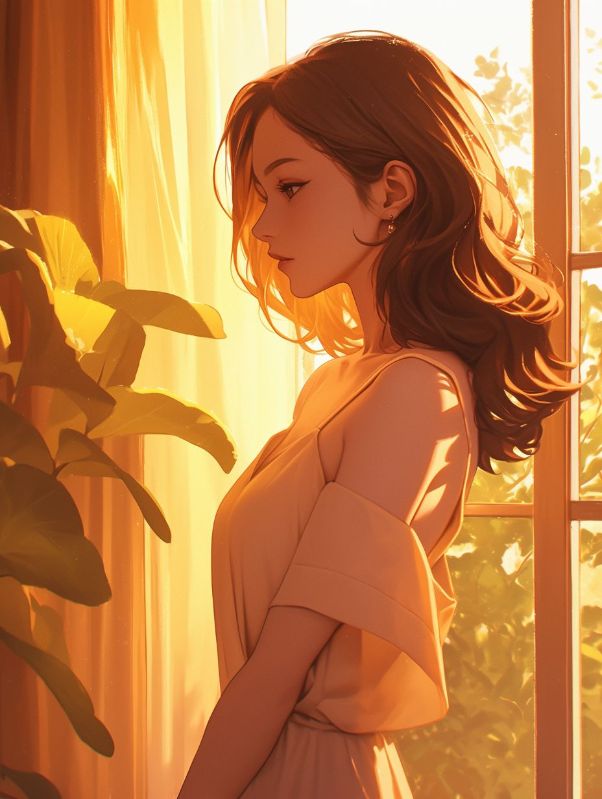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3
“喂酒有什麼意思?用嘴解腰帶,在場的所有人解開一個,我加兩萬。”
霍景淮拿出黑卡砸在我臉上,嘴角噙著笑,每個字像烙鐵一樣燙的我心臟生疼。
他身邊的女人露出驚訝的表情,躲在他懷裏。
“景淮,這樣會不會太過分了,怎麼會有人為了區區兩萬塊做這種事?”
“這點錢連買個包都不夠。”
霍景淮安撫的拍了拍她的後背。
“有的人天生下賤,你太單純了,怎麼能跟她比?”
區區兩萬塊?
兩萬塊可以讓我給我媽媽化療兩個月。
兩萬塊可以讓我交大半年的房租。
我數了數在場的人數,將近五六個。
“霍總說話算話。”
隨即彎下腰叼著身邊男人的腰帶。
牙齒在金屬扣上發出清脆的響聲,口水也沾滿了腰帶。
包廂裏響起更濃重的喘氣聲,跟我的口水聲交相輝映。
我感覺到身上遊走了許多隻手。
像惡鬼一樣抓住我的腳踝往地獄裏拖去。
霍景淮似乎沒想到我答應的如此幹脆。
眼神更加厭惡。
他看著我走向一個又一個的男人,動作越發熟練。
直到我走到他麵前,準備彎下腰時,被他厲聲打斷。
“沫沫見不得你這麼臟的女人,別碰我。”
我站在原地,嘴唇磨的通紅,下巴上還掛著晶瑩的水漬。
“謝謝霍總。”
我小腿發顫,聲音還是甜膩的道謝。
“都給我出去!”
霍景淮像是被我的笑容惡心到,忽然踹翻了茶幾。
就連他身邊的女人也被助理帶走。
整個包廂隻剩下我跟霍景淮兩個人。
“你現在這個鬼樣子,沒給你爸氣死嗎?怎麼,當初被我一語中的,真成了個爛人?”
我沒說話,隻顧著趴在地上找那張沒來得及收起的銀行卡。
說什麼呢?
說我爸是真的死了。
說當年那件事之後我媽身體每況愈下,最後得了癌症?
還是說我被學校開除,被專業拉入黑名單永遠不能找到工作?
他知道了會比現在還解恨吧,畢竟他姐姐的死,我爸爸也有份。
可我不想讓他如意。
霍景淮等不到我的回話,看著我眼裏隻有那張銀行卡竟然肯趴在地上,更加暴怒。
他抓起我的頭發,盯著我的眼睛。
“你他媽說話!溫以茉!”
我忽然笑了起來,還是那副嗓音。
“霍總,我叫茉莉。”